从驯兽牧马的戎狄到一统天下的王朝,深度揭秘秦国的起源之谜



本期话题
司马迁笔下的赢氏先祖是一群驯兽放牧、鸟身人言的夷狄,这个归化于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与艰辛,才最终成为秦国的创立者?

《史记》当中对殷、周和秦人起源的记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在司马迁的叙述中,这三朝始祖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帝舜时代的名臣。
殷商的始祖是帝舜时代的司徒殷契;周人则是那个时代的著名农师后稷的传人。至于秦人,“嬴氏”最初是帝舜赐予传说中佐禹治水的贤臣伯益的姓氏。

三朝始祖不但起源于同一时代,而且居然同朝为官,这样的传说实在不能不让人质疑它的真实性。
这些传说很可能出自于后人的杜撰。
因为在司马迁介绍殷契、后稷与伯益的身世时,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共同点就浮现出来了: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殷契的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而后稷的母亲姜原则是帝喾的元妃。
但如果你就此认为殷契和后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就大错特错的。因为这哥俩儿居然都不是帝喾的儿子。
确切地说,传说中的殷契和后稷都不是按照人类的有性生殖繁衍下来的后代。
《殷本纪》中说简狄在野外沐浴的时候因为吞食了一颗玄鸟诞下的卵,感而成孕,生下了殷契;
而姜原则是在野外踩中了一个巨人的脚印,鬼使神差地怀了后稷这个让她感觉不详的儿子(所以母亲给他取名为“弃”);
至于女修诞下伯益的传说,那其实是又一个“玄鸟陨卵”的翻版故事。

这些传说故事的共同点是,它们确切地指出了三朝始祖的母亲都是谁,但却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哪一位。
这很可能意味着商、周和秦都起源于古早的母系氏族社会。
在那个时代,人们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
而当历史推进到父系氏族社会,后人再回头追溯氏族的起源,他们的父系先祖遂变成了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只能靠传说和想象去补充了。

我总疑心,商、周和秦的先祖都同出一朝名臣的传说是来自汉代人的编排。
而之所以编排这样的故事,跟他们的高祖皇帝刘邦的出身可能有直接关系。
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帝,到公元1912年宣统退位,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一共四百多位。
在这四百多人里头,名副其实的布衣天子只有两位: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
蜀汉的昭烈皇帝刘备是不能算在里头的。因为他虽然是个卖草鞋的,但毕竟是刘氏皇族的旁支后裔,好歹也还得说是个破落贵族。
同为布衣天子,但刘邦和朱元璋在谈到自己的出身时,态度可大不一样。
在明太祖御制《皇陵碑文》中,朱元璋非常坦率地承认,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为了躲债而漂泊到濠州钟离的佃户,“农桑艰辛,朝夕彷徨”。
而刘邦虽然也是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小时候不但读不起书,甚至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但在《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中,他却成了赤帝也就是帝尧的嫡派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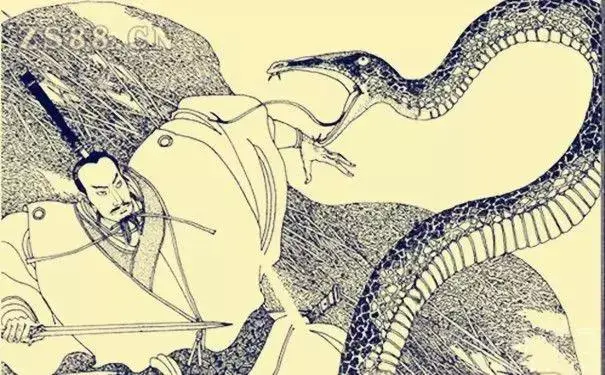
我们大可不必以道学家的眼光去表扬朱元璋的质朴和不忘本,也不必去批评刘邦的虚荣与夸饰,因为无论质朴或者夸饰,背后都有着深邃的政治考虑:
秦朝及其以前的朝代,把持政权的都是世袭贵族。
刘邦代秦而立,肈建西汉。一个穿草鞋的现在要去统治一帮穿靴子的,谈何容易!
“赤帝之子”就是皇帝刘邦的“新靴子”。编排这样的传奇身世并不是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是对世袭贵族政治的余威的妥协。
既然高皇帝的身世都可以这样编排,或许,当汉人重修前史的时候,也把这种习气带到了他们对商、周和秦的起源历史的叙述中也未可知。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手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提供一个假说,期待有抛砖引玉之效。

虽然,三朝起源的传说很可能出自于后人的杜撰,但这些传说中对殷、商和秦的民族性格的形容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
禹为司空治水,弃后稷司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先祖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
——《国史大纲》
殷契为司徒,职司教化,象征着殷商民族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后稷为农师,教民稼穑,寓意着西周这个农耕部落的勤劳笃实。而伯益是传说中的“虞人”,佐舜“调训鸟兽”。他的后代费昌和孟戏中衍还分别做过商汤和太戊两朝天子的马夫。

这些传说似乎暗示着我们,从经济形态上看,早期的嬴氏是一个以驯兽放牧为主的游牧部落。
而司马迁“或在夷狄,鸟身人言”的描述则说明,在文化特征上嬴氏属于归化于中原王朝的戎狄。
事实上,直到西周,中原诸侯谈到嬴氏的时候仍然称呼他们为“戎”。
同时接受着中原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互影响,这种华夷交融的特征从嬴氏部落最初兴起的时候便已经初见端倪。

自从孟戏中衍受到商王太戊的眷顾,质朴而勇敢的嬴氏部落便死心塌地效忠商朝。并且因为屡立功勋,逐渐跻身显赫诸侯的行列。
嬴氏对中原王朝最重要的价值是充当“以夷制夷”的急先锋。
到了商朝晚期,他们已然成为殷商镇抚西戎的主要力量。也恰是在这个时候,嬴氏第一次与崛起的西周打上了交道。
孟戏中衍的曾孙胥轩迎娶了申国先祖骊山的女儿,而申国正是西周的姻亲姜氏的封国。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胥轩之子中潏和西周保持亲善,也藉此为殷商王朝维持住了西疆的稳定。

但这种短暂的和睦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到了殷商与西周两大国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嬴氏左右逢源的好日子就算走到头了。
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左袒商朝。
中潏的儿子蜚廉和孙子恶来革都以材力侍奉殷纣王。结果在武王伐纣的时候,恶来革被杀,出使在外的蜚廉闻讯,也为殷商殉节。

在商、周两大国之间选边站队,对嬴氏来说当然是一次危险的赌博,不幸的是他们最终押错了宝。
商朝的覆灭带给嬴氏的不仅是亡国的耻辱,更是部落分崩离析的深重危机。
刚刚夺取天下的西周,对殷商庞大的残余势力相当忌惮。(在今天出土的西周金文中,周人称呼殷商为“天邑商”或者“大国殷”,而自称则曰“小邦周”,足见双方力量悬殊。)
为了削弱殷商的旧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周朝将殷商的遗民拆分,交给分封的诸侯国进行统治。
而《秦本纪》中记载,入周之后,嬴氏部落也分为了两支,除了留在陕西的一支人马之外,另一部分则迁徙到了山西。
我猜想,这样的迁徙很可能就是西周对嬴氏这个曾经在灭商战争中反对过自己的部落进行分化瓦解的结果。

落籍到山西的那一支嬴氏部落,直到周穆王时期才又再度崛起。
他们的领袖造父成为了周穆王的马夫。造父善御,一日千里,凭借着这个本领在平定东夷盟主徐偃王的叛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周穆王投桃报李,以赵城封造父,造父一族遂姓了赵氏,这便是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始祖。
从伯益的调训鸟兽到造父的一日千里,再到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氏一族一直保持着在马背上建功立业的光荣传统。

留在陕西的那一支嬴氏支裔则经历了更加曲折的沧桑变故。
他们虽然守住了先祖的故地,但是在新朝的处境已经与殷商时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他们是远离王朝中心的西垂诸侯,如今他们的聚居地犬丘却密迩王畿,与西周的都城镐京是如此的接近。
对眼皮子底下的战败者,周天子的感情可能相当复杂。
一方面,这个曾经与自己间接联姻的部落在武王伐纣的大决战当中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实在是不识时务的敌人。
但另一方面,长久以来镇抚西戎的经验与威望又让周天子难以舍弃嬴氏的利用价值。
究竟该如何对待嬴氏呢?
虽然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个颇费思量的政治问题,但是请不要忘记,西周和嬴氏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是长期僻处西戎,在与少数族裔的冲突与共融当中成长起来的。
因此这个问题上,周天子的分寸拿捏得非常恰当,那就是既利用,又防嫌。

那个曾经为周人与嬴氏牵线搭桥的申国又一次出马了。
周天子将申侯的女儿嫁给了嬴氏部落首领大骆的嫡子成为妻,再度建立起了双方的联姻关系。
另一方面,大骆的另一个儿子非子则被派往在汧、渭之滨,为周孝王养马。因为工作得力,周孝王将非子封到了秦邑,也就是汧水与渭水交汇的地方。
于是,“秦嬴”的称号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历史的记载中。

效命西周的经历,对陕西的两支嬴氏后裔来说都充满着压抑与血泪。

到了秦嬴的曾孙秦仲当家的时候,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西戎的激烈反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居住在犬丘的成的家族就在这次大规模叛乱中被全部消灭。
但是,遭受惨重损失的赢氏部落非但没有从周天子那里获得相应的抚慰,反而被迫继续为西周晚期的动荡与乱局买单。
当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登基之后,为了实现周朝的中兴,积极对外扩张,他利用嬴氏被西戎族灭的仇恨,任命秦仲为大夫,命他讨伐西戎,导致秦仲为西戎所杀。
秦仲的长子秦庄公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着四个弟弟和周天子派给的七千军队,终于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并因此获得了周天子可怜的封赐:将秦邑和的犬丘故地赐予庄公,号为“西垂大夫”。

用几代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西垂大夫”对秦庄公来说是一种耻辱。
这个名分意味着他只是一个依附于周天子的“家臣”,是一个安靖西垂的护院保镖。
当秦庄公带着一身的征尘与血污回朝复命,他却分明看到了周天子对秦人的傲慢:这个在殷商时代曾经堂堂正正的一方诸侯,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匍匐于天子脚边的粗鄙而低贱的奴仆。
为了摆脱西周附庸的卑贱地位,秦庄公和他的儿子秦襄公苦苦地等待了半个世纪。
直到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1年),昏庸的周幽王终于让老秦人看到了独立建国的曙光。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因为嬖爱褒姒,周幽王做出了废嫡立庶的错误决定。
周幽王将原来的太子废黜,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新太子。
这可是大大地惹恼了西周的姻亲申国。因为原太子宜臼本是申侯的外孙,他的母亲申皇后就是申侯的女儿。
废黜宜臼直接导致了申国与周幽王的决裂。申侯联合了西夷与犬戎,出兵杀死周幽王,并扶立太子宜臼即位新君,是为周平王。
在周幽王遭受犬戎攻击,举起烽火向各方告急的时候,拥兵自重的诸侯们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救驾。
倒是那个被王室瞧不起的秦襄公将兵救周,浴血奋战。
倘若不是秦襄公的出兵护卫,周平王是否能顺利地迁都洛邑尚在未定之天。

对救国于危难之中的秦襄公,周平王不能再像先王那样忽视他的存在了。
但是要封秦国为诸侯,两手攥空拳的周平王却实在是无地可封,因为此时都城镐京乃至整个宗周都还陷落在犬戎的占领当中!于是急中生智的周平王想出了一个画大饼的馊主意:“戎狄无道,如果秦能够攻逐戎狄,那打下来的地盘就全是你的!”
这个画饼充饥的赏赐不但暴露了周王室的衰落,而且在周、秦本不愉快的交往历史中又再添上了一笔阴暗的色彩。
但是看着周平王那张无赖的脸,感到羞耻的秦襄公仍然选择了与他盟誓,坦然接受这张空头支票。因为襄公知道,对即将诞生的秦国来说,一张合法的准生证是它将来融入中国大家庭的先决条件。
至于地盘,与戎狄征战多年的老秦人可不像周天子那样畏敌如虎。秦国的剑与犁,迟早会插遍关中这片四塞之地!

从双方歃血盟誓的那一刻起,秦国正式登上了春秋的历史舞台。
二十以年后(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击败戎狄,收复了宗周故地。
又过了七十三年(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将都城迁到了雍。之所以迁都,是因为卜辞中说:“都雍,秦国的子孙将来必定会饮马黄河。”
割据西方的秦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偏安的诸侯,它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黄河之畔的洛阳。那里是中原,是大禹九鼎和权力巅峰的所在!
从这时起,秦国那混合着泪水与欢笑,耻辱与光荣的东征岁月,即将拉开帷幕。
本文系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保护,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欢迎分享转发,您的分享转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