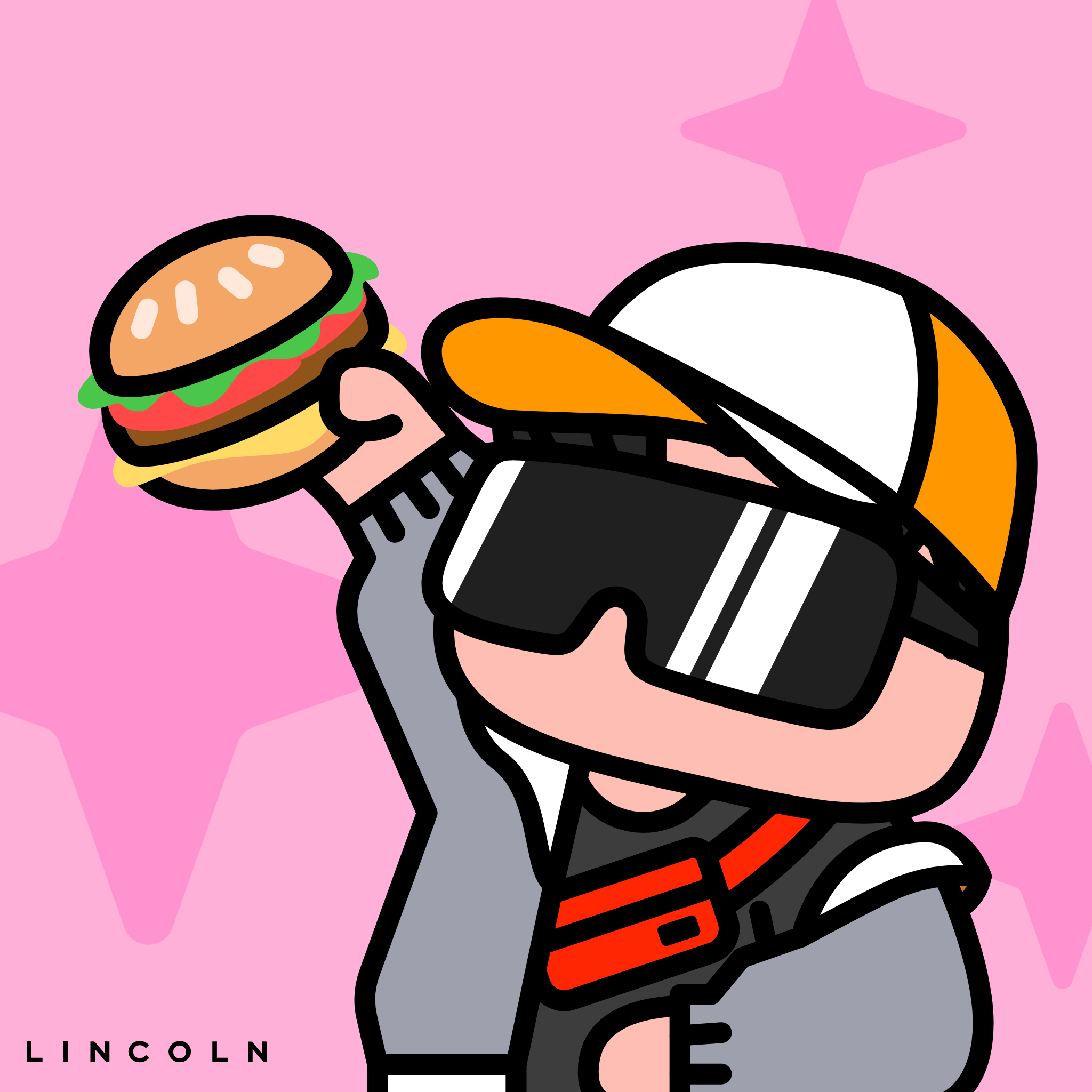加缪《第一人》第一部分读书笔记
第一部 寻父
贫穷是一座没有吊桥的堡垒。
学校向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逃离家庭生活的场所。至少在贝尔纳尔先生的课堂上,学校培育着他们身上孩童比成人更至关重要的渴求,即渴求发现。在其他课上,当然教会他们许多东西,不过那种灌输总有点像填鸭。做好的饭菜摆到他们面前,要求他们都囫囵吞下去。可是,在热尔曼先生(在这里,加缪无意间写上了现实中自己小学老师的名字,而不是原文里的贝尔纳尔先生)课上,他们第一次感觉出自身的存在,感觉出他们受到极大的尊重:老师认为他们有能力发现世界。他们的老师敬业,也不仅仅是为领取的报酬而教授他们,他直截了当接纳他们进入自己的生活,同他们一起度过自己的生活,向他们讲述他的童年,讲述他所了解的一些孩子的经历,向他们阐明他的观点,而不是强调自己的思想,例如,他跟许多同事一样,是反教权者,但是在课堂上,却未讲过一句反对宗教的话,也没有反对过任何可能是一种选择,或者一种信念的态度反之,他更加激烈地谴责不容置辩的行为:盗窃、诬告、口是心非、卑鄙下流。
一个多世纪以来,成批成批的人来到这里,开垦,耕耘。有些地方越犁越深,另一些地方却越折腾越浅,最后地面只剩下一层薄土,结果整个地区又荒草丛生了,而他们生儿育女,随后也消逝了。他们的子孙也无非如此。那些人的子子孙孙,也同他本人一样,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没有过去,没有伦理,也没有教导,没有宗教,但是乐得如此生存,乐得生活在阳光之中,面对黑夜和死亡而惶惶不安。所有这几代人,所有这些来自多少不同国家的人,在这已经预示暮色的灿烂天空下,没有留下痕迹就消失了,自生自灭。他们已经完全湮没无闻了。实际上,这正是这片土地的功能,这是随着夜幕从天而降的。而这三个人又走上村子的道路,看到夜色逼近而心情紧张,充满了惶恐。当暮色飞速地降临海面,降临起伏的高山和高原,这种极度的惶恐,就会占据非洲所有男人的心,也正是同样的极度惶恐,夜晚在德尔斐城腰制造了同样效果,建造起了神庙和祭坛。然而,在非洲的大地上,神庙已然拆毁了,仅仅剩下这份难以承受的温馨重重压在心头。是的,如同他们逝去!如同他们还要逝去!悄然离开,抛却世间万物,如同他父亲,死于一场不可思议的悲剧中,远离他出生的故乡,过了完全不能自主的一生,从孤儿院开始,中间经历了不可避免的婚姻,直到受伤死在医院里,围绕着他,由不得他构建的一生,直到战争夺走他的生命,埋葬了他,从此永远成为他家人和儿子的陌路人,他也皈依了无边的遗忘,遗忘便是他这类男人的最终家园,是始于无根的一种生命的归宿。
在岁月之夜中行走在遗忘的土地上,这里每个人都是第一人,而他本身,没有父亲,不得不独自成长,从未经历过父亲呼唤儿子等他长到懂事的年龄好对他讲述家庭秘密的时刻,或者讲述往昔的艰辛、他本人的生活经验。而这样的时刻,即使可笑而讨厌的波罗尼乌斯,在对拉厄耳忒斯讲起时,也一下子变得高大了。可是他,长到十六岁,继而长到二十岁,却没有任何人给他讲解,他必须独自学习,独自成长,增长力量,增强能力,独自找到他的道德和他的真谛,最终诞生为一个男子汉,为以后更为艰难的诞生,即开始关心其他男人,关心女人,就像所有在这地方出生的男人一样,有一个算一个,都试图学会没有根基、没有信仰地生活。而如今他们全算上,无不有可能最终成为无名者,丧失其经过这片土地的唯一神圣的印迹。墓地上夜色现在重又笼罩那些无法辨认的墓盖石板,应该教会他们关心别人,关心现在被排除掉的那些征服者群体,那些先行的前辈,现在他们应该承认,与那些征服者同一种族,同一命运。飞机现在向阿尔及尔降落。雅克想到圣-布里厄的那座小墓园,士兵们的坟墓比蒙多维的坟墓维护要好些。在我心中,地中海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在有限的地域,前尘往事和姓名都保存下来;而另一个世界,风沙在广袤的大地抹掉了人的踪迹。他曾力图逃脱湮没的命运,逃脱那种无知顽固的贫困生活,他不能生活在这种盲目忍耐的水平,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只顾眼前而毫无计划地生活。他跑遍了世界,曾感化、塑造、激发过人,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然而,他现在从内心深处知道了,圣-布里厄及其象征,对他从来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他想到他不久前离开的破旧、长了绿苔的坟墓,怀着一种奇特的喜悦,接受了这样的意念,死亡将他带回到他真正的祖国,并以其无限的遗忘,也覆盖了这个异乎寻常而又平凡的人的记忆。他孤立无援,在穷困中自强不息,成长创业,登上幸福之岸,以便随后在初晨的阳光下,没有记忆也没有信仰,独自进入那些人的世界,进入他的时代,以及他那可怕而又激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