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生存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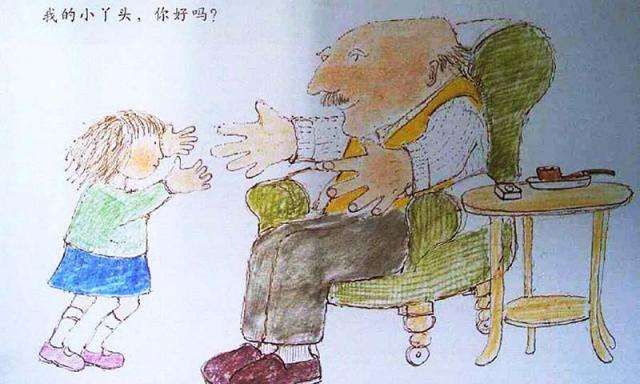
外公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正值日军进犯的前夕,然后又爆发内战。待到内战平定,外公已经是一个少年了。建国初期,外公考取了国家飞行员,却又因为他母亲的担忧,就留在家乡教书、延绵子嗣。
那时的外公,正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娶了外婆,隔年诞下了大舅舅,把学校发下的精粮拿回家搭配着外婆挖空心思才做出来的杂食,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也就是他的母亲和他们在那十多年间相继出生的六个孩子。
然而,待到外公的而立之年刚过,就爆发了为期十年的文革浩劫,按照外公的那轻描淡写的说法,就是那十年吃了玩,玩了吃,在县城的教育组里居闲职,等待复学。却又因为受人陷害,被圈进了山区家乡的某座大山里边改造学习,一待就是三年,而这十余年的时间里,虽然是工资照发,但意味着什么,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文革结束,外公已经是过了自己最好的十年,奔五的人了。可能,他那时的生活哲学就已经成型,那即是风潮之中的人生,安稳就是幸福,默默保持自己,向世界妥协,读书也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然而,事情并不是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是又开始了另一阶段的极限循环,因为那时外公外婆的孩子们渐渐大了,该是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时候了。拿外公的话来说,就是那时的他并不如何地期待重新回去教书,反倒是宁可在家里守着外婆和孩子们。然后就是教育组的专员来登门邀请,外公的答复很简单,如果能给我搞到树,我就去,去哪里都无所谓,因为要准备起新房子,给儿子的婚事做准备了。
因此,在那十年的黄金时期过后,外公外婆开始了持续又一个十余年的操劳,两个儿子的房子,四个女儿的嫁妆。紧跟着,孙子辈的也一个接一个来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时也就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开始慢慢放开。可是,这也并没有为农村带了太大的改变,反倒是因为农民谋生方式的单一,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跟不上,造成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而这个过程中,最受累的还是外公外婆,因为除了大舅舅一家和另外两个远嫁的姨妈,我们这一辈的表兄妹,无一不是被父母扔在外公外婆那里,寄养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两三年不止,因为他们都要外出挣钱。
也就是在九十年代后的这三十年,村子里边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可外公外婆依然坚守在我们童年寄居过的土胚房子里边,看着他们诞下的两代人在生活里边沉浮,可也只能是这样地看着,小表哥溺水,大舅妈病忘,二女婿中风,然后在他们八十一岁的这一年,白发人送黑发人,未满六十周岁的大舅舅心肌梗塞猝死。
当头发稀疏花白的外婆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吟哦着牙齿掉光、双唇萎缩的嘴巴,含着浑浊的泪水向我哭问的时候,我难过得扭过头去不作回答,因为我真就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呀,只能重复着说不要难过,外婆说这可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呀,看着他从一尺多长长到如今,话都没有留下一句,怎么能不难过?
可能吧,生活总要折磨得让人对一切事物都失去信心,才能教会一个人站在远处去观察自己生活的智慧。可是,当我们真的在某一天,看清了人生的荒诞和无奈时,才恍然发现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了。然而,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停止,停止的只会是我们的自然生命的消逝带走的那无法割舍的牵挂和思念。
外公年少有志,耽于堂前尽孝;青年有志,囿于国事;壮年有志,为儿女操劳;老来赋闲,却又儿女四散;古稀之年,儿媳长子相继无常……
大概,这就是人生的本来样子吧。
读书为报国,然身陷囹圄,所以六个儿女无一通理;盼儿女成人,却又为礼事所疲,妥协于人之常情;待得儿女成家立业,风潮又起,看着他们浮沉而独自心酸;期颐之年只盼能守着两个小重孙明理成人,却又要承受丧子之痛。
命运,可能在我们每一刻的畏惧之中就已经注定,在每一次的失望之中,我们就小心地偏移一点航向……可是,似乎只是为了保全活着的满足,仿佛也是一件登天难事,而这大概就是人生吧。
武汉 2016年7月28日 整理 2016年7月30日星期六
外公的生存哲学的评论 (共 9 条)








- 浪子狐 推荐阅读并说 :欣赏佳作,荐读,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