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昨夜漫天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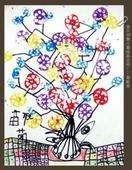
——追忆《诗刊》编辑李小雨老师,兼忆编辑往事一二
-
-
如果从国内诗界“广角”说,在李小雨近四十年《诗刊》编辑生涯里,得到过她帮助的作者不计其数,(李小雨于2015年春节前夕在京遽然去世,年64岁,刚离开《诗刊》不久,尚在中国诗歌学会负责,令人万分惋惜,——因李小雨已成一个“符号”,一个自1980年以来全国很多作者们与《诗刊》、与诗歌界联系的耳熟能详的“符号”——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一个角度回忆出她与诗歌、与自己成长的某些丝缕脉络,我只是有幸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在她身边工作过五年多,仅从我了解的角度谈一点。
-
谈到李小雨的编辑素质,我认为值得学习的一是她对艺术的“兼收并蓄”的态度,对传统、新潮、半新不旧等各种诗歌均能欣赏,唯只要写得好,我以为这主要来源于她一代(50年代出生)的经历学养,及她前面老一辈诗人的“真传”,承继了《诗刊》历史里的某种东西;二是“任稿唯贤”;三是深刻同情与倾身底层的作品,她对来自于农民、工人、打工者、士兵,甚至失业者等作品,很有天然性感情,耐心扶植。还有一点最难学,她几乎从不在自己编辑的刊物,及国内她熟悉的刊物上登自己的作品,(她写过很多诗歌,积压下并不发表),身为编辑一生成功地避开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诟病(如果当“编辑”又兼“作者”,会陷入此特殊职业要求的矛盾与尴尬)——这个牺牲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
《诗刊》编辑每周一三五坐班,余时自行看稿,加之李小雨的国内诗歌活动多,与她见面的时间就很少,打交道几乎一律是“送稿子”,既送报经过编辑一审看过的稿件。李小雨那时是编辑部主任,她对编辑的管理马马虎虎,但对你的稿件却异常认真。而她本人除去开会全部时间都在看稿、看稿,即使你午休去,也从不见她吃饭甚至喝水,只埋首桌子上大摞大摞的稿件(北京的许多文学刊物闹“稿荒”,但《诗刊》的每日稿件“铺天盖地”),一次听她与外地作者谈,说她每天后半夜2时才睡觉,因睡不着在看稿。她上下班挤公车拎着两个“北京大妈”买菜布袋,里面塞满了待审的诗稿,在国内我几乎从未见过这么“苦待”自己的文学编辑,后听人说她的父亲住院,她晚上去照看也坐在医院走廊椅子阅稿到夜深。
-
-
李小雨不喜欢编辑在稿签上敷衍两句,而是希望提出认真有见地的意见,我以为这是《诗刊》的一个老传统,所以报送的稿子都要先思考一下,说出具体特点、不同于其他处、有的还附上作者年龄、地域、艺术特征等,以使主审时能尽快把握要领。李小雨特别欢迎手下编辑给她多送稿,见面不是先看你人,先看你手里的稿件(因为报送的稿件越多,编辑部选出好稿的“几率”越大)。
-
回忆起来我在70年代末的东北就知道李小雨的名字,最先应是阅读她的父亲李瑛先生的诗歌,充
满激情且细腻与艺术化,李小雨作为《诗刊》著名的女编辑那时也闻名遐迩。后来直到1996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时,才初次见到她,她担任学院的外请诗歌辅导老师,她与很多学员的年龄也相仿,她讲课及课后交谈均很平易没一点编辑架子,学员们多不叫她老师而直呼“小雨”,她愿讲真话办事也态度负责,学员把厚厚的一整本打印诗稿给她,她也不厌烦百忙中说拿回去看。
-
我初次到李小雨的位于中国文联大楼内的《诗刊》去,实在无法想象她的主任室简直是一座小型“书稿库”,里面堆满了书籍刊物、从地下堆到天棚的巨量稿件(其中有很多成捆的及装在袋子中的),中间只有一条小道勉可通过,我很担心作者来访抽烟时引发火灾,奇怪的是文联大楼竟不管她而她竟能从这书稿堆里准确地找出她要的东西,令惊奇(积压的稿件她会反复拿来挑选,以不浪费)。
-
-
来《诗刊》造访的作者很多,李小雨是一个天然富有耐心的女编辑(以前我见到梅绍静也很耐心),很少“分别心”,对谁都一样,沉静地倾听,访客比她说得多,她只是听或微笑并不打断。外来的作者们与她即使是初次会面也会很快放松,觉得她甚至比作者本人还腼腆,她着装简朴,态度庄谐,谈话给人直率和毫无机心感觉,这些都一下子抓住作者令他(她)们永远不能忘怀!作者们认为遇到了诗歌界一位难得的“老大姐”。她认识的作者们诗人们遍布全国甚至港台,有的很有地位或金钱,但我从未听说她除了工作范围请人给她办一件私事,她给我的印象是永远没有“私事”,有一年她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北京没有工作,有人说你求求人呀,她说求谁呀?我听了感慨系之(那时她已是《诗刊》副主编),她根本就没学过怎样经营自己的“私事”(!)
-
-
2004年初我到《诗刊》工作,李小雨对我送的稿子并不十分满意,她认为我选的东西太偏,太边缘,与主流刊物宗旨不符。但时间久了,她觉得我送的稿件,并不是刻意要把所谓“民间”的东西“偷运”进《诗刊》,而是从刊物的角度考虑,进行“补缺”。这与我的编辑稿签说明有关。在各种艺术、各个流派、新与旧的兼容上,我与她的观点也多有接近处,她对于“民间的”东西,并无特别的看法与排斥,但要求作品必须出新,这是个恒定标准。作为资深的权威,李小雨对国内诗歌“面上的”情况的掌握我们穷其一生也追不到,但她仍愿意倾听编辑意见,我曾向她推荐过原生态乡村诗歌、广东及长三角“打工诗歌”,当然也包括70后及地域诗歌,80后及网络诗歌,还推荐过译诗、回忆录随笔等。她对我送来的稿件基本信任,一般不会怀疑有挟私,因为我从未因任何一件稿子向她说过情,这违反我的编辑原则,一“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二好作品自己会开口讲话。
-
李小雨当过知青,当过兵,后又考入北大,多年基层阅历使她对广阔社会生活有深刻体察。我给她送报的稿件,一般先阅过三遍,第一次印象好放在抽屉里,过一段再看二遍,第三次仍觉得好填好稿签送报。她把自己的几厚本分省《全国作者通信录》借给新来的年轻编辑“约稿”用,我做文化工作多年从报社到刊社从未见过此事,这是编辑很私人的东西呀,(有人竟把它当个人“财富”),怎么可以共用?由此可见一点李小雨的特点。关于评价当代诗人,她倾向于哪个诗人的哪几首诗篇更好,而不是概念化地把当前“当红”的二三十个诗人简单排个序,她认为知名度不高或无名作者也会写出传世之作。
-
偶听一次李小雨谈及她的父亲(她很谦虚几乎从不提及大诗人父亲李瑛):说她父亲退休前中午从不休息,利用午休写诗,父亲认为工作时间是领工资的属于公家,写诗得占用个人时间。——我听闻印象很深(人们说她的出身贵为将军级别,而她作风如此朴素,“与民平等”,身上无“骄娇”二气,这是大家最服气处)
-
在李小雨为《诗刊》留下的遗产里,我认为她坚持的办刊的美学方向、编辑作风很重要。有次她曾说过当代诗歌要“大气”,我理解这个“大气”,是指主流诗歌殿堂倡导的美,应是国色天香的美,不是东倒西歪的美。她对真善美的坚持是一流的,对假丑恶的东西绝不放行,美学基础是建立在多数人(大众)的审美情趣上,并以悲悯情怀为浓重底色,这些体现在她的选稿倾向、卷首语、评语、栏目设置……等。
-
在编辑会上,李小雨请编辑提出改善刊物的意见,记得我提过几条:一是刊物的“组诗”后应附加作者简介,以加强解读;二每期最好有一两篇诗歌随笔;三每期应有一个页码的“诗坛简讯”;四开辟散文诗页;五要刊登点外国诗歌及随笔类译笔。以上有的采用了,有的没有,有的采用一段停止。我个人觉得一本刊物怎样办,主要决定于它的历史和传统……。对了,有次我还提出一个建议,建立《诗刊》的小型历史展室,收集自1957年以来的资料以免流失殆尽。
-
-
建国后“主流诗歌”经历三个时期,一是“黄金时期”,既《诗刊》自1957年创刊,到贺敬之发表《雷锋之歌》时期的热情高涨60年代上旬至“文革”前,那是“革命文化”加“集体文化”,诗歌共鸣感最强时段;二是文革后《诗刊》复刊后不久经历的70末“新诗潮”期,此时思想活跃,禁区冲破,艺术叠新;三是90年代至新千年前后的“过渡地带”,市场在前,文化滞后,诗歌读者少,艺术歧见多,诗无定论,诗少共鸣,缩成一个个“圈子”……(以上个人见解)。李小雨经历了《诗刊》文革后复刊至今的后两个时期,但她成功“对接”了第一时期(既传统期),在中国“主流”诗坛里,她可谓老一辈诗人的“接班人”,其作风主旨有连接昨天的桥梁作用。她是一个诗人,诗歌编辑家,诗歌活动家,使命家,许多当代著名诗人的作品都经由她选发(有的“诗名”后来超过她),似乎就是主流诗歌所灌注进的“一个灵魂人物”,到最后越过公元2000年后,“将诗歌进行到底”、和“把一切献给诗歌”都做到了。她在《诗刊》长期任编辑,后中晚年做到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等,但一生始终在默默做“嫁衣裳”,从青春时代在北京虎坊路《诗刊》旧址到中国文联大楼,40年来她已经成了诗歌爱好者们珍藏记忆的一部分(她身上集合着知青、军人、严格家教的“革干”子女身上某些优秀素质,是50后“特殊材料炼成的”一代中佼佼者,并把这些品质投诸忘我的当代文化事业,随说一句,李小雨一生担任过好多国内诗歌奖项评委,但我似乎从未听说她自己获奖,是出于偶然?还是高度自觉?)
-
-
(……彼时,在北京虎坊路老《诗刊》旧址的平房院落里,那时候老诗人们还活着,烟斗,藤椅,常青藤,与来访的青年诗作者侃侃谈诗,沉沉论道,直到黄昏与夜深。远方,京都已灯火阑珊夜色迷离……更高远处,一批星雨滑落天际岁月潮涨潮落生命轮换不息——)
-
——不知觉中,我一代(50年代出生的)也为诗歌走向远方,做完了“命定的”一份……
-
在编辑的送稿签上,李小雨的批语,有时三言两语,有时一大段,(甚至比编辑写得还长),提醒应该注意什么,哪里下次要改正,编辑要小心“错别字”千万别让她的红笔碰到!(我猜这也是老一辈诗人的严谨“做派”)……
-
-
诗歌是给人们造梦的。编辑部是让梦出发的地方。给青年们的每一封回信都是对梦的极大鼓舞!作品必须反映生活——是李小雨的一贯要求, 对美的不息追求——是李小雨的永无止境,——谁在敲门呀,今天又什么好稿带来吗?(忽伤怀:君今遽然辞诗界,再有好稿可送谁)……
-
-
……观看李小雨编集一期新的《诗刊》,犹如观看一位指挥员在作战室情景:摊开军用地图——一摞摞稿件,桌子上、沙发上凳子上、甚至地下都摊开一层,这里是随记的纸条,那里是剪刀、浆糊,(她不喜欢电脑),电话在叮叮,没工夫接,到处纷沓杂乱,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她的凝神静气……夜深了,她还在干,而明天一本崭新的《诗刊》就要送交印刷厂飞转的轮机!……李小雨精力充沛,年轻时就是一个“铁姑娘”(70年代对山西大寨妇女主任郭凤莲的称谓),从不生病,工作起来务实耐久,仿佛是一个专为某种事业而铸造的“器皿”……
-
“有形终归灭,不灭惟真空”,作为共和国的第一批“理想主义”者中的文化者,很多离去的身影们包括李小雨不过比我们先走一步,(虽然她走得还太早,太匆忙,本可以为诗歌事业再做一些),人生就是要多赶几次“场”(一位体育迷的话),艺术就是要多赴几次“盛宴”,(——而其余的琐屑又何足挂齿!)……所幸我在她的演出还没谢幕前碰见了她,那华采,那风范,永留舞台。
(2015年4月——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