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呛人生》:得不到爱的东亚人,可以拥有发疯自由吗?

朋友们,《BEEF》(怒呛人生)看了吗?
跟以往的美剧题材不太一样,《BEEF》不再脸谱化展现温和勤劳的ABC,而是展示了身为亚裔的「复杂性」,聚焦于主角内心的挣扎和外化的疯狂,中间还穿插了不少吐槽心理咨询的金句。
今天的推文想要结合剧中的人物和情节,观察当代人精神状况的同时,分享一点心理学小知识,没看过也是完全可以食用的。
当然,还没看过且不想被剧透的朋友,现在点个收藏退出也还来得及!


故事由一次别车事件开始,史蒂夫扮演的丹尼倒车时堵住了路口,黄阿丽扮演的艾米则用喇叭狠狠嘲讽了他,丹尼回呛,而黄阿丽挑衅的中指则把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两人因此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式的路怒,把邻里乡亲吓得够呛,并因此结下了「beef」。

明明是一场小到不行的摩擦,却让以温文尔雅著称的东亚人变得冲动无比。当然不是两人不懂得礼让,而是他们内心早已压抑到了极限,随时都要崩溃。
戴着八角金丝眼镜的艾米生活看似优渥,实则四处漏风:艺术家丈夫乔治妈宝且没有天赋、全靠自己养活;气度不凡的婆婆在生活里出现指手画脚;可爱温柔的女儿却十分缺乏安全感;富甲一方的金主女老板也难以捉摸……
作为艾米对照组的丹尼,人生则失意得可怕:无所事事的弟弟成天除了打游戏就是捣鼓数字货币;自己建筑承包商的生意濒临破产,成家的期望对于没有异性缘的他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收留表哥做非法生意黄了自家旅店,年迈的父母被迫回到韩国……

路怒事件发生的当天,丹尼就像是一根过度绷紧的弦,随时都有断掉的可能。而艾米的一根中指,则让他松开了最后的理智、彻底释放出心底深处的愤懑,狠狠踩下了油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两人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内心的崩坏本质上却没有太多不同。他们彼此厌恶,却又承受着同样的压抑和痛苦。他们互相报复,却又在无形中成了支撑对方活下去的理由。
主角身上那种难以摆脱的沮丧感,也让观众直直地看到他们内心的挣扎,孤独、焦虑和失落感。这些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负面情绪,让人感同身受。
豆瓣上有条高赞评论是这么写的:“东亚人还没携手发疯是世界上的另一大奇迹。”


《怒呛人生》用一整季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虽然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经常被描绘成“模范少数族裔”,但他们却对自己拥有的生活往往不太满意。
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尽管亚裔美国人在教育和收入方面优于白人,但亚裔美国人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却低于白人。在国外出生的亚裔比白人更容易不快乐,而本土出生的亚裔则比白人更难感到非常快乐。
那么,亚裔压抑的源头是在哪里呢?
比起白人的“享乐主义”,东亚人更中庸平和,相信祸福相依,否极泰来。在西方信仰中则相反,好坏的互相转化是不存在的,变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永久性转化的线性概念。
社会心理学研究者认为东方人的辩证思维,即认为过于快乐可能会引发坏事的思维,导致他们遇事犹豫不决,最终显著降低他们的幸福感。
剧情中,丹尼一直幻想着自己如果像她一样富有、事业有成并婚姻美满,一定会感到平静和快乐。两人在阴差阳错地参加同场聚会后,丹尼动情地向艾米提问,“我想知道你幸不幸福?我有没有可能和你一样?”

艾米没有正面回答这个提问,而是化用了北欧神话告诫丹尼:“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都会消失。我们只是一条衔住自己尾巴的蛇。”
衔尾蛇象征着建构与破坏的往复,生命与死亡的交替,也代表着艾米认为自己的幸福随时可能消散。
幕后主创李成真在采访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意向:“这种(不安感)也是准确反映了我自己的生活。过去我是一名在纽约生活的无业作家,生活非常窘迫,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即便现在我有一部在网飞播出的作品,这种感觉仍然存在,甚至可能更加强烈。”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感觉永远不会消失。

况且在大多数亚洲文化中,幸福和福祉来自于社会中他人的义务和认可。个体是嵌套在关系、家庭、群体、体制的网络中的,家庭作为社会比较的最小单位,对一个人施加着莫大的影响。
一项研究测量了亚裔学生和欧裔学生感知父母期望的程度及其对主观幸福的影响。亚裔美国人报告称,父母在他们身上有特定的期望,他们更有可能无法满足这些期望(Newman, 2019)。因此,他们报告的幸福感受水平低于欧裔美国参与者。
这种家庭给予的期待无疑推高了优绩主义下东亚人内卷的动力,也让他们加倍的痛苦。
艾米的日裔艺术家丈夫也未能幸免,乔治作为精英阶级的代表,心底却住着一个患上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的小人,内心却非常空虚,害怕会被人们“识破”自己的光环。
当丹尼认可他的作品是“真正的艺术品”之后,他终于有勇气袒露自己的脆弱:“有时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你懂吗?我爸去世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里的,是他会不会带着对我的失望离开……”

这种对家庭认可的渴求,也构成了两位主角巨大压力的来源。身为移民二代的他们,除了实现“美国梦”式的成功以外,一个迫切渴望通过买房得到韩国父母的认可,另一个则希望得到艺术家婆婆的肯定。
在东方传统文化和美国社会的双重期待的塑造下,他们必须给自己带上一张情绪稳定的假面,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言语进行自我规训。
显而易见的是,当他们主动或被动戴着面具生活时,并不快乐。


艾米在多次去心理咨询后,终于忍不住向咨询师抛出了那个东亚人的究极拷问: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无条件的爱么?
毕竟对于东亚人来说,有附加条件的爱实在是太常见了。
“如果我没考上(研究生),是不是这一切就不存在了?”
“我现在得到的所有好处是因为他们爱我,还是因为慕强? ”
“所以他们真的是因为我考上了才喜欢我吗?这比不爱我更让我难过。”
“如果我落榜……我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会听见家人的叹气和埋怨,甚至被剥夺自我决定和规划的自由。”
这是一位名叫Karen的女孩在三联上的投稿,考研上岸后的她,因为在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开始真切地怀疑爸妈是否真的爱自己,还是爱那个可以让他们脸上有光的“优等生”。
与女孩的迟疑和空虚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评论区的网友,言之凿凿地把女孩的烦恼称为“凡尔赛”“矫情”“想太多”。

显然,在网友眼中,父母有条件的爱是正常的。所谓“无条件的爱”只是一种对无底线溺爱的修辞罢了,考研上岸的女孩属于得了便宜还卖乖。
艾米和丹尼也都内化了这样一条准则:努力工作和持续牺牲是让他们值得被爱的原因。因此,他们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各自的事业中,而不是花时间面对内心的空洞。
但内心的空洞是如此巨大,让他们不论取得多少世俗成就也无法填满,于是他们一次次寻求来自周围的认可,希望可以逃离这可怕的空虚,但逃跑的姿态只能让这份空虚加重。
而这份缺失也通过代际模式传递了下去。艾米在成长缺少爱的后果之一,就是她也无法很好地包容女儿的行为。在层层包裹的“精心照料”之下,女儿琼依旧复刻了艾米的童年,通过藏匿包装纸来掩盖自己乱吃巧克力,生怕因不听话失去妈妈的爱。

和望文生义产生的歧义不同,无条件的爱(unconditional love) 是指对另一个人表达爱,而不考虑它将如何使自己受益或获得回报。更多时候值得是一种行为(behavior),而不是一份感受(feelings)。
当人们寻求无条件的爱的时候,并不是寻找一份没有底线的溺爱,而是希望能得到一份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爱。
只因为我是我,所以你爱我,这种确认感在东亚社会中尤为稀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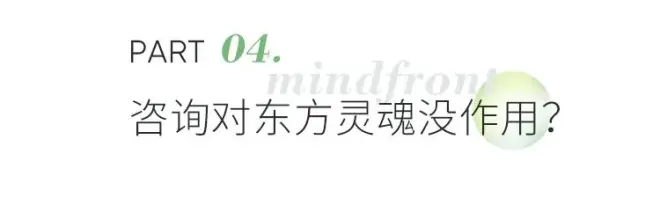
丹尼在剧中曾高谈阔论,西方式心理咨询治愈不了东方人的灵魂。(“Western therapy doesn't work on Esterm minds”)。
在艾米身上,这句话仿佛得到了应验。婚姻出现危机,丈夫把艾米拖去参加夫妻咨询,她在咨询室中否认有抑郁的征兆,只说了些她认为咨询师想听到的话。

透过这次咨询,很轻易就能发现,东亚人很难在咨询师面前真正放下心防。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压抑是了如指掌的,可以比咨询师更主动地头头是道地分析,但却从来没有试图真正地打开自己。
咨询师李松蔚把这样看似积极的来访者,称之为控诉者(accuser)。他们并不想做出改变,只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面对这样的来访者,即便经历丰富的咨询师也是非常难入手的。
事实上,心理咨询不是用来指责我们的父母或文化的工具,它是帮助自我进行觉察的起点。如果来访者不愿意袒露自己或由于耻感无法做到诚实(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咨询就无法奏效。“我都来心理咨询了,怎么还要我努力?”
这对任何来到咨询室的来访者都是如此,无论种族,族裔或文化背景,并不是说心理咨询针对亚洲人无效。

最后一集中,艾米和丹尼服下了野生浆果,在神经毒素的作用下他们产生了人生交错的幻觉,终于试着敞开心扉第一次真正地袒露自己内心,并在交谈中两人真正地达成了和解。
这种浆果代表的致幻剂也逐渐应用在了精神障碍的治疗中,特别是涉及裸盖菇素的研究,人们发现裸盖菇素对大脑功能,特别是大脑的默认神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产生了深刻且有意义的改变——这与抗抑郁药物的效果一致。
几个双盲对照的二期研究中,对癌症有关的社会心理痛苦的病人进行了迷幻剂辅助心理治疗,包括由癌症或其他疾病引起焦虑和抑郁障碍(C/I-RADD)、重度抑郁症(MDD)、强迫症(OCD)、物质使用障碍(SUD),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抑郁的积极缓解,且没有引起严重的不良事件。

虽然神经科学和医学(诸如致幻剂)的研究在不断突飞猛进,让人们不断向心理健康的一端靠近。但心理的临床治疗也并非是一项万能的技艺,和现代医学一样有自己的局限,比如时代造就的心理症候群。
在一百年前,人们不需要面对互联网,也不会面对如此撕裂的政治文化差异,也不用忍受科技生活所带来的副作用,太多的疑问是新出现的、暂时无解的、需要时间的。
大火的咨询师崔庆龙在采访中提到过心理咨询的局限:“我觉得咨询师也挺无力的,更多的问题回答不了。心理学面对的问题已经是最末端了。”
崔庆龙也表达了自己的期望:“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更多优秀的社会学家,更多优秀的架构设计师,他们可以从结构层面去优化,也许只是一个参数的调整,就能把很多微观层面的东西解决掉,甚至都不会产生出来。”

在理想国降临前,面对时代的滚滚车轮,每个人都必须或长或短地面对那个把自己困在原地的「系统」,独自承受着专属的那份压抑。
如果发疯的片刻,能够让当代人短暂地脱离“笼子”,来表达自己内心难以言喻的情绪,尽情释放压抑已久的压力,得到一点点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东亚人偶尔发点小疯,也未尝不可。

References:
Ng, Y. K. . (2002). East-asian happiness gap.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7(1), 51-63.
Theory? https://positivepsychology.com/coping-theoryCherry, K. (2022, May 24).
Monk prayogshala research institution. (2022). “Because I’m Happy!”: Happines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non-weird-science/202204/because-i-m-happy-happiness-in-the-east-and-the-west
Medical Review:
Mindfront Psychotherapist Sophie D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