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

書評:《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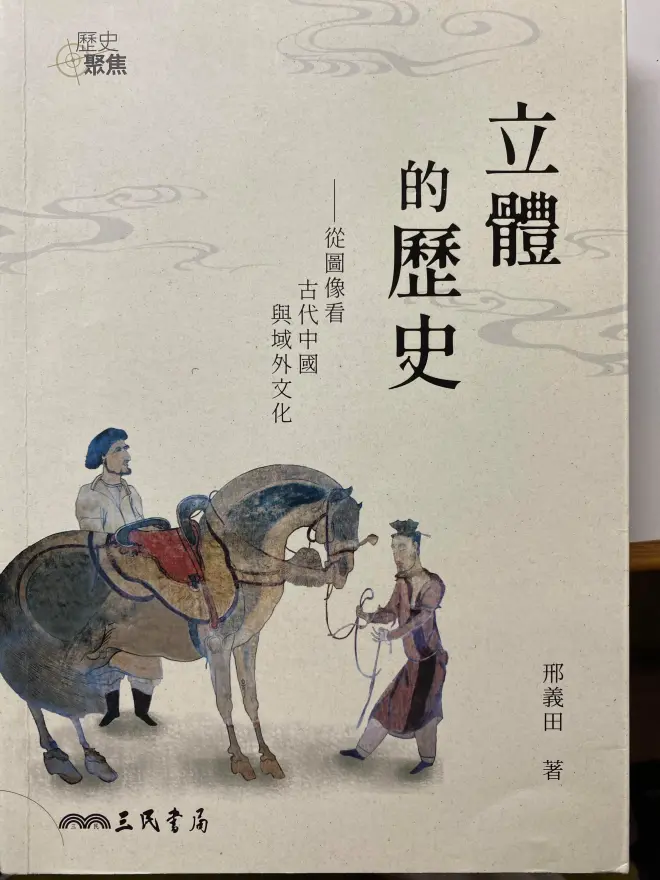
一、何謂「立體的歷史」?
本書四講改編自作者的著作《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2]中的四篇論文,用淺顯易懂的口吻敘述,也能貼近讀者。作者在開場白中強調書名「立體的歷史」是指文字、非文字與史家,同時也是材料、讀者與寫作者三者的互動,兩者都強調透過不同角度描繪出一種整體歷史畫面。然而光是描繪是不可以的,史家仍要受限於材料本身,因此作者如何運用與呈現材料描繪「立體的歷史」,以及作者運用哪些新文化史視角,我將在下文中討論。
二、圖畫,史學家的另一隻眼
在傳統蘭克實證史學研究中,主要關照文字材料,對於非文字的史料基本上不太在意,而在年鑑學派鼻祖布洛克的觀點[3]認為歷史研究的證據,不應該受限於文字,舉凡人類活動的痕跡都該被史家所關注,也就是說,非文字材料也能為歷史研究使用。本書四篇文章共同的特點,就是這種新研究方式的使用,即運用圖像、石雕等各種非文字的史料,彌補傳統歷史研究中缺乏文字史料的問題,而且圖像相較於文字能帶來的視覺效果更大,並且更能傳達文字無法描述的細節。
像是本書第一講,中國古代猴能避免馬瘟的文化母題,如果從文字材料來看,只能追溯到北朝《齊民要術》,然而圖像資料則可彌補文字史料的不足,例如出土瓦當與畫像石上的猴在馬廄等,使猴與馬的母題能夠追溯到戰國時期,連帶顯示當時草原與農業之間的文化與商業交流;在第二講則是透過墓葬壁畫、陶俑等非文字資料討論胡人左衽的問題,因為服飾這類日常生活的事物,一般來說比較少被刻意敘述在史書中,所以運用當時人們留下的圖畫或陶俑,都一定程度反映時人對服飾的理解,並以此作為討論的依據。



在第三講中作者以披著虎皮帽的力士唐三彩為起點,在唐三彩缺乏史料記載的藝術母題上,透過其他地方類似形象的雕塑的樣式,為其找尋母題來源;而第四講前半段中,從希臘陶片流放制討論中國漢代百姓的識字率問題。作者從類似的字跡討論,因為字跡也是一種圖像,背後所蘊含訊息甚至大於文字本身,像是書寫者是誰,以及誰能讀懂等。



三、觀看域外,另一個立體的視角
本書除了運用圖像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域外」與中國比較,主要分成三個層次,首先是一、二講的案例,域外與中國是有直接且密切的接觸,不論是貿易往來,還是統治征服,都反映出與兩者是屬於共構[4]的狀態,第一講關於中原地區工匠為遊牧民族製作工藝品的案例,則是這個看法的註腳之一。在第二講則提及胡人服飾的問題,可以體現出「社會認同存在於細小的差異中」[5],而服飾本身成為歷史討論的客體,除其代表了文化,同時也反映穿著者的心態[6],例如擁有左衽墓葬壁畫的墓主,可能不接受漢人文化,或是生活在胡漢界線較為模糊的社會環境中,不須藉由特定服飾標榜自己文化認同身分。
前兩講是位於邊疆與中原之間的文化互動,接著討論後兩講則分別為歐亞大陸兩端的文化,第三講是論及文化傳播的過程,力士形象不斷的經由內陸亞洲的諸文明「移譯」[7],在希臘化與羅馬帝國向外輸出文化與佛教傳播,最後成為那尊唐三彩藝術形象的來源;第四講則是從西方歷史中一些線索,激發探討中國歷史的問題意識,例如漢代識字率與代筆問題,或是從羅馬的禁衛軍案例探討漢代皇帝身邊的護軍。
而這樣運用域中域外、東西比較的書寫方式,則可以給讀者一種全覽歷史的感覺,一如作者所言描繪整體的歷史。
四、物質文化進入歷史研究
本書運用的圖像史料,除了圖像本身帶來的視覺效果外,相片中的各色器物,如石雕、帶勾、衣衽等,都是物質文化。而這樣物質文化的交流過程,是近年新文化史的轉向[8],從以往總是強調觀念演進的新文化史常會脫離社會本身的侷限性,而顯得管中窺豹,若加上物質的條件我認為有兩個好處,一是物質受限於當時的社會生產能力,不同生產力的文化接觸時,器物之間的工藝能探究其來源並反映文化之間的交流,例如第一講的中原仿製的猴型配飾;二是承接蔣竹山整理學界對物質文化轉向的說法[9],新文化史多了物質條件,也能較直觀的展現觀念是如何被賦予與論述在物質,例如其所蘊含的權力關係,以及透過受到當時社會具體使用過的器物材料,也能更加細微的比較觀念在實質運作上的差異性。
例如作者關注衣服左衽的問題,若是只依照文字中對胡人「批髮左衽」刻板印象,而不讓當時的胡人透過他們的衣著方式發聲,我們就難以看到服裝是如何從中性工具變成文化認同的符號,以及後來在胡漢之間文化差異下服裝的變化與妥協方式。
五、由本書走回《畫為心聲》
本書因為考慮讀者的緣故,加重圖像的使用比例與簡化的敘述方式,使得讀者或對於相關議題不太熟悉者面對圖像的視覺證據時,能夠快速找到這些看似繁雜圖像的共性。不過我認為此書作為回歸原作《畫為心聲》這部大部頭的著作,具有前導的作用,使讀者能夠抓住該書運用圖像史料的脈絡與作者的書寫邏輯。

後記(2500字之外):
邢義田教授的退休生活還蠻有趣,因去年疫情使他只能用電腦作研究。前些日子看到教授在用谷哥地圖找尋漢代外長城的具體經緯度,找了三個月甚麼都沒發現,直到年初到香港作尋訪學人,閒來沒事就給他找到了定位長城遺址的有力證據,障塞遺址。而這類研究也大概是近十年才開始的,過往的外長城遺址大部分是屬於考古學的範疇,當代學人比較少將其與歷史文獻連結。最後,在講座結束,他說自己的退休生活是在遊戲人間。


附錄
書摘(2500字之外):
本書是作者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的文稿整理,共四講分別是〈「圖像與歷史的研究」之孫悟空篇〉、〈想像中的「胡人」—從左衽孔子說起〉、〈希臘大力士流浪到中國?〉與〈他山之石—古希臘陶片流放制與羅馬帝國禁衛軍〉。
作者首先闡釋題名「立體的歷史」來自於文字、非文字與史家,或是材料、讀者與寫作者三者的互動,以展現三維整體的歷史畫面;承接運用非文字材料視角,開始討論弼馬溫與孫悟空關聯,弼馬溫諧音避馬瘟,而猴子與馬之間的關聯,若從文字來看能溯源到北朝《齊民要術》,但從圖像材料下手則可溯源到戰國時期北亞胡人與中原地區關於養馬知識交流,而胡人與馬的造型母題也流於中原。回到猴與馬的母題,除防疫外也產生「馬上封侯」意涵。
再者討論衣衽方向的文化,右任被視為華夏,與之對應左衽被視為胡的穿著,左衽孔子則被視為蠻夷統治的產物,但根據胡人的畫像史料發現,衣衽方向是左右並存,胡族本不在意方向,而是與漢文化衝突時才被強調。在胡漢互動下作者推論圓領、交領與對襟等無衽的衣服形制,是為妥協方案。此外,也探討胡人帽子的問題。總之,衣著作為一種群體的區分符號,人們以模式化的認知,也會加深對他群的刻板印象。
接著從武士俑談起東西之間的文化交流,作者發現這尊武士俑的藝術形象非中原母題,卻可追溯至希臘神話的大力士,手持棍棒身披獅皮大力士形象。在希臘化與羅馬帝國時代,因統治者喜好,該母題被反覆強化,並被傳到遠方。而因為中亞犍陀羅藝術,英雄力士成為佛教護法,伴隨佛教進入中原,力士頂戴也從西方獅皮變成中原虎皮,不過其保護者的形象仍舊未變。
第四講分為兩部分,以西方歷史為他山之石,探討中國古代史的問題。先是在陶片流放制中發現可能是代筆的現象,探討漢代在使用行政文書時,基層官員與百姓的識字率問題,以及聽在訊息傳遞的意義;再來是從羅馬的禁衛軍與國家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理解漢代護軍與事隨人轉的特性。
最後作者認為這四講強調從非文字與域外文化的視角來看中國歷史,便能夠勾勒出較深廣立體的歷史畫面。

[1] 邢義田,《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21)
[2] 邢義田,《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
[3] 參 馬克.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社,2020),頁75-80。如書中將歷史研究比喻成在實驗室做完實驗後,觀察實驗殘留物或「痕跡就如記號,是感官可知覺的;是無法接觸的某些現象所遺留下來的」等句,都隱含歷史研究不該只限於文字,而該有視覺性的觀察。
[4] 王明珂,《華夏邊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頁7-9。序文觀點主要放在人類生態的角度下遊牧民族的經濟問題,以及與中原王朝的互動,形成一種共構的狀態。但我認為馬猴的文化母題就是因為共構的結構,得以傳遞到中原地區。
[5] 彼得柏克,《甚麼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100。引布爾迪爾說法。
[6] 彼得柏克,《甚麼是文化史》,頁96-100。書中舉法國貴族服飾之例。
[7] 彼得柏克,《甚麼是文化史》,頁167頁。簡言之,移譯的概念主要是將他文化中的某個物件,從原來文化的背景取出,運用在自己的文化中,並且不考慮其物件在原先背景中的脈絡,因此移譯是一種拼湊的過程。
[8] 蔣竹山,〈瓷器、菸草與白銀:物的全球史〉,收入氏著《裸體抗泡》,(臺北:蔚藍文化,2016),頁265-268。本章是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評論。卜正民運用畫作中的物件來看十七世紀的海上貿易,是同一時段橫跨世界的比較,而邢氏的著作偏向綜觀時間與空間比較,在物質文化的研究轉向來看,後者比較符合這類轉向。
[9] 蔣竹山,〈瓷器、菸草與白銀:物的全球史〉,收入氏著《裸體抗砲》,頁265-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