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图馆】代魏立晋 第十节 废立
本期作者:锦帆游侠
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未经授权,禁止二传,违者必究
曹芳很愤怒。
自己好歹是一个年过二十岁的皇帝,养父曹叡在他这个年龄登基,很快就摆脱了四位辅政大臣(曹真、曹休、司马懿、陈群),将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汉武帝刘彻更是在他这个年龄颁布推恩令,开始从诸侯王手里收回权力。我曹芳就是再平庸,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二十岁青年,都不会甘心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
然而举目四望,曹芳发现,大部分朝臣迫于司马师的威势都噤若寒蝉,他很难找到足以信任的人。
但还是有的,中书令李丰就是一个。
李丰,字安国。在当时,是和夏侯玄并称的名士,时人把他们并称:夏侯泰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夏侯玄好像怀里有日月一样光彩照人,李丰颓唐不振的时候仿佛玉山将要崩塌一样。连曹叡都把自己唯一的亲生女儿嫁给了李丰的儿子,李丰的名声之高,可见一斑。

然而,中看不中用。
还在正始年间,曹爽和司马懿在尚书台展开明争暗斗的时候,李丰夹在中间左右逢源,最后为了躲避是非干脆请病假,按照当时的制度,请假超过一百天,这官你就别做了,老实回家呆着养病去。李丰想了个办法,每次请病假都不超过一百天,每次算着日期快到了,病突然就好了,过了几天又装病接着躺,就这么反反复复躺了几年。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等司马懿解决完曹爽,得知消息的李丰马上就蜷缩在地起不来了。怕事到这个地步,李丰也算是独一份。
等司马懿死后,曹芳需要寻找自己能倚仗的新的力量,有人就推举了李丰。李丰觉得自己皇亲的身份也足够显贵,加上攀附上皇帝这棵大树,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便慢慢开始向曹芳靠拢,起了扳倒司马师的心思。
但毕竟李丰是只耗子,面对司马师这只大猫,要起打猫的心思,得积攒足够的力量。李丰看上了两个人:国丈张缉和太常夏侯玄。
张缉是李丰的老朋友,两家住的也很近,李丰暗地里让自己的儿子李韬联络张缉,恰逢张缉生病,借着探病的名义,李韬向张缉说明了来意。张缉沉默良久,还是表了态:“我们同舟共济,还有什么能逃避的呢,只是我担心这件事不成功,就要祸及宗族啊。”至于夏侯玄,之前夏侯玄就写信给李丰抱怨过自己的处境:曹爽死后,自己就因为是曹爽的表弟,才干无从发挥,还被自小的好友司马师猜忌,两人自此产生了极大的裂痕。李丰并不担心夏侯玄会不会支持自己的计划,不过出于保险,他并没有让夏侯玄知道自己的全部计划,只告诉了他一个大概,并没打算让夏侯玄完全参与。

说穿了,不管是张缉还是夏侯玄,都只是拉起来旗号,利用他们的身份标榜行动的正义性,真正要干事,得有军事力量。
环视一圈,李丰发现他所能倚仗的力量只有两支:一支是他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一支是他的好友,中领军许允。分别代表了地方和中央的势力。
李翼当然不会反对哥哥的计划,但当李丰找由头召李翼进京朝见,借机带兖州军入京时,引起了司马师的警觉,被否决了。
只能倚仗许允了,不过李丰并不知道许允的态度,打算试试他的深浅,他派人伪造了一份诏书扔到许允府门口,大喊一声:“陛下有诏!”就跑了,许允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任命夏侯玄为大将军,许允为太尉,共同录尚书事。”要知道,这时候的大将军是司马师,太尉是司马孚,诏书是什么意思,许允心里一清二楚。
看到诏书的许允吓了个半死,赶紧烧掉诏书。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司马师。
这就是曹芳所能倚仗的力量:花瓶李丰一家、有名无实的张缉和夏侯玄、以及不敢惹祸上身的许允。
但曹芳仍然决定动手: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压制了他理智的思考。
嘉平六年的二月,计划正式开始实行,李丰的方案如下:皇帝即将选贵人,按照曹魏的礼仪,司马师必须亲临皇宫朝贺,趁大将军进宫的机会,调集宫门的卫兵,将司马师就地斩杀。为了保证计划的成功,李丰还说服了宫内的三名宦官:苏铄、乐敦、刘贤,说服的理由也很简单:“你们平时在宫里没少干坏事吧?大将军这个人严肃毅重,知道了绝不会放过你们,看见张当的下场了吗?那就是你们的榜样!当然你们也不用怕,只要协助我除掉大将军,你们就能升官。”三人唯唯诺诺,当即答应。
这种事儿,要么不做,要做就得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例如高平陵这样的大事,老狐狸司马懿在做之前连自己的亲儿子司马昭都没告诉。反观李丰,为了策划这件事,除开夏侯玄、张缉等人,还让一些宦官也参与了进来。知道的人越多,泄密的速度也就越快。密谋很快传到了司马师的耳朵里。
司马师问自己的幕僚王羕:“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王羕:“请让我一个人去请李丰过来。”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能来?”
“他如果没有准备好,迫于形势,一定会来,就算不来,我一个人也足以制服他,但是一旦让他知道了事情败露,率兵直入云龙门,挟持天子登凌云台,调动凌云台的三千禁军起事,那就不是我能解决的了。”
司马师点点头:“既然这样,你去吧。”
果然不出王羕所料,李丰面对司马师突然的召见,毫无准备。心存侥幸的李丰还是跟随王羕上了车,一起去见司马师。
与此同时,许允也得知了李丰被请走的消息,他准备去见司马师捞人,但又害怕司马师的威势,虽然已经出门,犹豫了许久,还是回到了府上,最终没有去见司马师。
唯一能救李丰的人选择了退缩,等待李丰的只有死亡。
一见到李丰,司马师问:“你竟然敢谋杀我吗?”
李丰知道事情败露,破口大骂:“你们父子狼狈为奸,要谋逆社稷,只可惜我力量不足,不能抓住你们这群混蛋!”
司马师勃然大怒:“打死他!”
两边的侍卫用刀环猛击李丰的腰部,一通暴打,把李丰打了个鲜血淋漓,没过多久就咽了气。
当晚,司马师下令把李丰的尸体送到廷尉处审理,廷尉钟毓看见眼前这血糊糊的肉团子,拒绝接收:“这人没经过廷尉审理就被处死了,还送我这儿来干什么?”钟毓也是个明白人,这事儿是个烂摊子,司马师是打算扔给他来收拾残局,还是趁早推脱开。
司马师派来的人连忙解释:“中书令打算行刺大将军,大将军出于自卫才把他打死,更何况,这儿有大将军的敕书。”
这下推脱不开了,钟毓勉强接下了李丰的尸体。
这边曹芳得知李丰被活活打死,当然明白是司马师下的毒手,勃然大怒,打算召来廷尉探查李丰的死因。郭太后迫于司马师的权势,当然不会放曹芳冲动行事,死活才把曹芳拉住。
当然,钟毓是不会动司马师的,经过“探查”,将李韬、李翼、张缉、夏侯玄、苏铄、乐敦、刘贤全部捉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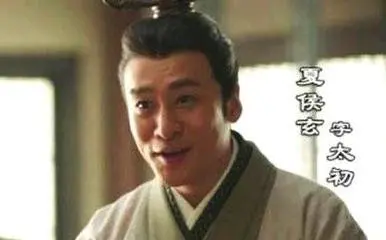
当然,最重要的是供词,钟毓盯上了夏侯玄。
在狱中,钟毓开始做夏侯玄的工作:“泰初,你还是招供了吧。”
“我没有参与,招什么供?既然钟君做了大将军的人,你想给我安插什么罪名,就自己写吧。”
钟毓知道,他曾经的偶像夏侯玄志向高洁,终究不会写下供词。当夜,钟毓亲自给夏侯玄写好供词,泪流满面送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很快看完,微微点头:“就这样吧。”我认了,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参与进去呢!也许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也不会让魏室衰弱至此吧!
伴随钟毓而来的还有他的弟弟钟会,一直以来,夏侯玄都是钟会非常崇拜的人,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和夏侯玄相交都被夏侯玄拒绝。此时有这样一个机会,再次去亲近自己崇拜的人,钟会兴奋不能自已,举止开始不庄重了起来。夏侯玄立即正色:“我虽然是罪人,也不敢这样,还请钟君端正自己的举止!”钟会羞赧退下,他知道,当初那个怀抱日月的夏侯玄,再也不会出现了。
过了几天,钟毓上奏:经过审讯,苏铄交待李丰劫持陛下,刺杀大将军,大逆不道,罪证坐实,请定罪名。于是召开朝会,讨论结果是:除开给先帝唯一的骨血长公主留下血脉,除了李韬的三个儿子,其余李丰、张缉、夏侯玄、乐敦、刘贤全部夷三族,其余亲属流放乐浪郡。考虑到张缉是国丈,给他留个全尸,赐他自裁吧。至于张缉的女儿,也就是曹芳的皇后,立即废掉。
临刑的那一天,刑场上一片哭哭啼啼,只有一个人仍然面色不改,神色自若,没有丝毫畏惧。
此时,司马师府上,司马昭不住在给这个人求情:“泰初从小就和我们交好,请哥哥考虑到昔日的情分,放过夏侯泰初一马吧!”
司马师没有作声,反过来问身边的叔叔司马孚:“我的才能可以控制夏侯玄吗?”
司马孚回答:“当初司空赵俨葬儿,你来的时候只有一半的人出来迎接你,等夏侯泰初到了,所有人都站起来迎接,从声望看,我觉得你不行。”
司马师看了一眼司马昭,没有说话。
司马昭明白了,他的哥哥和父亲不一样。父亲有足够的威望与功业支撑他的声望,而兄长没有父亲那样的资本,必须以铁腕的手段处置一切,去扫清一切阻碍他登上最高峰的人。只有用无情的手段消灭一切公开反对势力,才能将权力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司马昭似乎明白了什么。
当然,夏侯玄也明白司马师不会手下留情。当初司马懿去世的时候,许允曾经恭贺夏侯玄:“太傅死了,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夏侯玄叹了一口气:“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太傅尚且能以通家之好对待我,司马师兄弟是不会容下我的。”
随着夏侯玄的死亡,曹魏最后一个声望极高的宗室重臣灰飞烟灭。
接下来就是许允了。
司马师不动许允,并不是不想动,而是许允身为中领军,掌握着兵权,不好轻举妄动,得用点手段。
过了几天,许允接到了一封调令,让他出任镇北将军,前往冀州。同时司马师亲自给许允写信:“虽然镇北将军一般没有什么重大军务,但毕竟是军事重镇,现在足下出任本州,正可谓衣锦还乡。”许允大喜过望,本来就巴不得离开京城远离是非,真是想瞌睡送来了枕头。有人提醒他不要大意,但许允已经被冲昏了头脑,根本不以为意。和曹芳一顿唏嘘离别之后,刚踏上路上没几天,许允就收到了新的目的地:监牢。
“许允私自挪用公家财物,徙边!”接到诏令的许允一脸懵逼:说好的镇北将军呢?
哼,还想镇北将军?命都不打算留给你。
在前往流放地的路途中,许允不明不白死在了路上。
许允死后,曹魏不再设置中领军,皇宫外围禁军的兵权全都交给了担任中护军,司马孚的次子司马望。
狠,真狠。
处理完朝臣中的反对势力,接下来就要处置反对势力的幕后boss——曹芳了。但毕竟曹芳是当朝皇帝,要下手,第一得有名义,第二得有兵威。
名义上来说,辅政大臣有纠正皇帝过错的责任,如果辅政大臣认为皇帝不堪其任,在得到朝廷大多数人认可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废立,最好的标榜例子就是伊尹和霍光。权臣对皇帝进行废立,大多以这两位作为榜样。司马师作为曹芳的辅政大臣,是有这样的权力的。
然而,难处就在这个“得到朝廷大多数人认可”。曹芳执政期间叫停了曹叡时期的大兴宫室,言行举止遵从礼法,还遣散奴婢,拿自己的私房钱充实军资,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那就只能用强硬的手段逼迫太后和群臣认可了,而要采取这个手段,司马师必须倚仗弟弟司马昭在许昌的大军。东关之战之后,司马昭的这支军队就驻扎在许昌以备不时之需,是司马师足以倚仗的力量。
机会来临了。这一年的六月,蜀汉的姜维率领大军再次进攻雍州,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到了九月,胜负还没见分晓。这就给了司马师很大的机会,他有名义调动司马昭的许昌军前往雍州退敌,而许昌前往雍州,京师洛阳是必经之地。
曹芳其实也在打这支军队的心思,假如借着去平乐观阅兵的机会趁机拿下司马昭,用许昌军来对付司马师,不失为一个反戈一击的机会。
几天后,司马昭的大军浩浩荡荡来到洛阳城外。望着平乐观台下黑压压的大军,曹芳退缩了。原本写好了缉拿司马昭的诏书,曹芳几次准备去拿,又缩了回来。这个年轻人心里内心在经历极大的波动:有多少人能站在我这边帮我呢?
最终,曹芳没有动手,最后的机会就此消逝。
有了司马昭的大军做后盾,司马师的底气顿时足了起来,他让人拿着废掉曹芳的诏书前往永宁宫,去找郭太后。
此时郭太后和曹芳都在永宁宫,来人直接告知太后:“大将军准备废掉陛下,立彭城王曹据为君!”
曹芳很清楚自己的命运,没说什么,起身退下。
郭太后有点生气,“把我当什么了?”来人继续说:“太后没能教好陛下,现在大将军心意已决,外面大军已经整军待发,太后听大将军的就好了,还多说什么?”
郭太后表态:“那让我见见大将军,我有话说。”
“有什么好见的!拿印绶来盖章就是!”
太后默然无言,让随从取出印绶交了出去。
司马师大喜过望,立即召集群臣开会。
会上司马师开始了精彩的表演,痛哭流涕对群臣说:“太后认为当今圣上不理政事,沉湎女色,德行有亏,准备废掉当今圣上,你们怎么看?”
群臣心里很明白司马师的想法,纷纷跟上表态:“这事儿只有听从大将军的意见啊!”
“承蒙大家抬爱,我这就当仁不让了。”
于是司马师写好废掉皇帝的奏章,以太尉司马孚带头,群臣联署,送了上去。曹魏的第三代皇帝曹芳就此被废,成为齐王,在洛阳城边的金墉城渡过了他的余生。
接下来就要考虑新皇帝的人选了。权臣立新皇帝,基本都想立年幼的皇帝,方便控制,而彭城王曹据作为曹操的儿子,神童曹冲的亲弟弟,已经年近五十,司马师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这是司马师以退为进的办法。立小皇帝,自己的野心暴露的太明显,既如此,不如利用郭太后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只要提出立彭城王曹据,郭太后就不能再以太后的身份听政.司马师相信,对权欲和地位尚有眷恋的郭太后不会同意立曹据的提议,一定会立比她辈分低的宗室,这样,司马师的意志也就通过郭太后的欲望得到了实现。
果然,郭太后上了套。
司马师的使者前来请印绶的时候,郭太后趁机表态:“彭城王按辈分是我叔叔,如果立他当皇帝,我去哪?而且总不能让明皇帝绝嗣,我看立文皇帝的孙子,明皇帝的侄子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更加合乎礼法,请大将军考虑一下。”此时高贵乡公曹髦年仅十四岁,作为曹丕的孙子,曹叡的侄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无论是郭太后听政,还是司马师辅政,都是名正言顺。
这正中司马师下怀,司马师同意了。
几天后,高贵乡公曹髦从邺城来到洛阳,眼看要到京城,进京的前一天晚上,曹髦考虑到玄武馆前殿是先帝昔日休息的地方,拒绝了群臣让他在此休息的安排,在西厢房休息。曹髦的侍从上前恭贺:“群臣打算用迎接天子的礼节迎接您呢!”

曹髦正色道:“那可不行,我是公侯,不能用天子的礼仪。”
第二天,群臣在洛阳城门夹道相迎,拜伏在地,曹髦见了,连忙下车还礼。
侍从提醒他:“您马上就是皇帝了,按礼节不用还礼。”
“我还没正式登基,怎么能不还礼?”
当车驾到达止车门时,曹髦端端正正下了车。
“您不用下车。”
“我被太后宣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然要下车。”
就此,展现出高尚礼节的高贵乡公曹髦成为了曹魏的第四任皇帝。
司马师的愿望实现了。
但,世事总会在各种方面开这样那样的玩笑,对司马师也不例外。
“你见过陛下了,你认为陛下是怎样的人?”司马师问前往朝觐的钟会。
“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才气和陈思王曹植并称,武略和太祖曹操并称。
评价极高。
司马师的脸色转向了阴沉:“那真是好事呢。”
不过司马师顾不上这么多了,因为,淮南,又一次起风了。
参考资料:
1.《三国志》,(晋)陈寿,(南朝宋)裴松之注
2.《晋书》,(唐)房玄龄等
3.《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4.《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校标注,(清)余嘉锡笺疏
5.《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