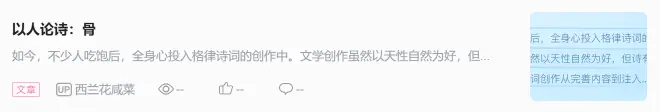以人论诗:肉
肉
掌握格律后,就迎来诗词游戏的下一关卡——丰富内容。内容相当于诗词的“肉”,依附于骨,千姿百态:可吊古哀人,抚今追昔;可观山海、谈天下;也可伴小酒几杯,叙一己情思。各人经历、处境不同,诗词内容看似无法可考,实有规律可循。
内容离不开描写,描写离不开角度。选择描写的角度,关键在于把握好“我”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正是: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以物观物,则物即是物,我即是我。
王国维将这两类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实为老文人的矫揉造作。这些老文人总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大部分玩家只想知道怎么赢,老文人们却高高在上,天天分析游戏历史、设计理念,就是不讲怎么玩,连个快捷键都不给。
再者,“可堪孤馆闭春寒”是写诗人不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写诗人爽。诗词都是人写的,哪有什么真正的“无我”可言。它们只是撰写内容的角度不同。
“有我”写景,常用寒鸦、苦月、雁悲嘹。“无我”不会刻意强调个人感情,不会过分将一己感觉加于事物之上,而是通过事物本身潜移默化地抒情写意,也只是一种手法,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说到底,还是角度问题,即摄像机应该怎么摆的问题。
以李煜为例,他的后期诗词,大都是从“有我”角度去写,万事万物皆浸透了他的亡国哀怨。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此类描写,是把摄像机架在主人公面前,录下他的满面愁容;再把摄像机推开来,去录周围景色;最后,在处理时加上一点点回忆。21世纪初的一些言情剧也擅长此类角度;近来,由于质量下降,影视剧纷纷改用大量对白填充内容,没有几个会走心讲究机位切换了。
对事物描写,在“无我”角度把控得最好的,当然是李白。如“黄河落天走东海”“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是熟练掌握航拍及超广角拍摄的诗人之一。他描写事物,就是架着滑翔机,开着超广角镜头,在空中录下来。人们之所以称他为诗仙,大概也和他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飞行模式有关。现在,央视一些关于大好河山的纪录片拍摄也是此法。
当然,作为创作者,角度并不只是摄像机怎么摆,还要重点解决“拍谁”这个问题。刀法再好,要做排骨却削下一块蹄髈,岂不成了笑话。
同样是宇宙浩渺,若写鲲鹏,则垂翅千里,激水万丈,一年一返;若写蜉蝣,则晨昏暮霭,轻扬红尘,朝生暮死……
且以一幅三峡水墨画而言,描写应有重点,不能左一笔、右一画,填了半天只知道自己写了三峡,到底写了什么却不清不楚。胡诌几句中不溜的诗句为例:写山则是“扁舟几叶腰间过,忘数星辰驻桨声”,写舟则是“两岸危岩过,扬帆到楚天”,写水则是“千岩万貌由谁改,又载轻舟向日出”。
把最想切下来的内容想妥,找好角度切下,再根据相应格律加以完善,诗词的内容关就算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