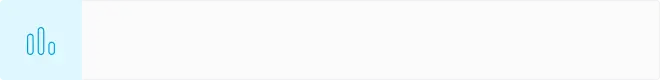拉普兰之鹰 01 阴云密布

注:本文为架空历史,与真实历史无关!

“万没想到,我们第一次面对战争竟然是这种鬼样子。”佩卡闷闷不乐地说着,把自己的军用水壶和弹药包等等挎在身上。此时正值深夜,帐篷里只有一点点光亮,每个人都在低头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事实上,在夜幕掩映下的营地中,每个人都在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这是1941年2月,战争的阴云将随时笼罩在芬兰的大地上。苏军在边境陈兵数十个师,而芬兰对外发言人却严正地拒绝了苏联人对卡累利阿和佩察莫的领土要求。此时,自冰冷的北冰洋到最南面的库班草原,没有一处的边境线上不是这样地沉闷而无语。没有所谓的摩拳擦掌——因为战前的火药味太浓了,没有人能脱得开身去培养什么激情。
有人走出帐篷,在雪地上摔了一跤。营地刹那间如被冻住了一样寂静无声,每个人都把耳朵竖了起来,默默祈祷着。没有预想中的脚步声或者其他的声音,在听到雪地上那个人慢慢爬起来后,小小声的议论来了又去,收拾的声音又悄悄地响了起来。
佩卡把所有的家当都收罗好了,转身踏步,在帐篷门口向外偷偷看去,刚才摔倒的那个人正站着仰望夜空。
“嘿!”佩卡悄悄喊了他一下,那人没动。他直接溜到那人背后,轻轻拍了下他。痴迷于拉普兰的星空中的年轻士兵终于回头了。原来是阿克塞尔。
“在坦佩雷恐怕看不到这样好的星空吧!”佩卡打趣道。
“看不到哦。”阿克塞尔说着,眼睛还是没有离开星空。佩卡感觉被噎住了一样,默默地看向天上,满天星斗如流萤般绚丽,相比来说,更加洁白的雪地反倒是显得苍白扭曲,甚至是恐怖。这么一想,佩卡反倒是不想要再看地面了。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仰望着。也许是无话可说,也许是不知说什么更好了。

“少尉,”马尔库斯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抬头看去站在面前的竟然是营长,“你们收拾好了吗?”
马尔库斯慌慌张张地紧叩双脚,敬了一个军礼并喊出:“收拾好了!”
周边所有人都被吓得一激灵,马尔库斯也很快意识到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然而,面色凝重的营长似乎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有的那么烂的脸色,从周边的人的眼光来看,营长更关心的是那两个在外面看天的傻小子。
“凌晨三点,全营会开拔,作为先头部队进入萨拉。行动要有足够的隐秘性,你们排是先锋。把你的人分成两个半排,两点半让第一个出发,一刻钟后你带第二个离开,去萨拉的第6营营部报到。记住,好好隐蔽,不要走大路,更不要在这种能被俄国侦察机随时发现的雪地里站着不动!”营长说着,瞪了马尔库斯一样,背着手从帐篷里快步走了出去。
佩卡和阿克塞尔还在看着星空,两个傻小子在雪地里像块木头一样杵着,一动不动。
“要把他们喊回来吗?”一个军士问马尔库斯。
“算了吧。”他回答。
两点半时,由一位老军士领着的第一个半排出发了,过了一刻钟,马尔库斯带着剩下的人悄悄离开了营地。整个营地像死一样静谧,谁也猜不出这里面竟然住着近一个营的人马。就算俄国侦察机来了,也会以为这是空的嘛,马尔库斯想。

等到拂晓快降临在萨拉时(恐怕离天亮还远得很),马尔库斯的排终于进入了萨拉。说实在的,所谓的“拂晓”在此地不过只是半夜的样子,然而凌晨四点还是太早了。老军士和那半个排已经等在那里一会了,看来是遇到了点问题。
“你们来干什么?这里肯定会成为前线。”喝的醉醺醺的第6营的传令兵问他们,“俄国人在对面少说也有两个师,我们在萨拉才三个营。不要说阻击了,我们就是挠痒痒的。总部肯定会让我们且战且退的。城防?胡说八道。”
“难不成你想在这里当个酒鬼,被俄国人的大炮追着屁股打?”老军士问他。
“又如何?把一个又一个先遣营调到这里,终究是要给俄国人的坦克垫脚的嘛,”传令兵说,“不如趁现在回去,也许你们还能逃出生天,多活一段时间。”
未知的俄国坦克让芬兰士兵们不由得不寒而栗,连老军士也没有说什么。
马尔库斯上前一步说:“这是约尔马营长的命令。我们只管执行,还请你让我们去报到。”
传令兵看了一眼他,不情愿地挪开了路,进去的士兵每个人都瞪了那酒鬼一眼。
第6营的营长很亲切地招待了马尔库斯的排,据说他是木匠出身,是出了名的好脾气。马尔库斯看了看指挥所里面的各种手工打造的家具,大概能明白这位营长的冬天大概是过得很滋润的。这位营长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木制的沙盘模型,沙盘上是用四块木板拼合雕塑成的萨拉周边的地形图。
那营长指着沙盘说:“看到这里了吗?这是一个哨站,从萨拉向东走大概几里就是了。我们在萨拉东面没什么成型的永备工事,只靠这个哨站提供情报。门口有几辆卡车会送你们过去的。我们营要转移阵地,你们负责接防,希望在天亮之前,我们的人都能回来这里。”
马尔库斯敬了一个礼,然后带着手下离开了。出门时,那传令兵说:“你们不会是要去东面的哨站吧,不会吧不会吧,那你们可惨了,哈哈哈哈哈......”老军士推了他一把,这人趔趄了一下,歪在墙边笑呵呵地继续喝酒,满带着假装出的谄媚姿态向他们挥手告别。
卡车在雪地上颠簸着,前方勉勉强强能看到一点点光,大概是那个哨站。等到车停稳了,所有人跳下车时,马尔库斯才发现哨站的士兵早就在门口列队等着了。所有人都一个个急着搓着手,在雪地里看起来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寒冷,然而从他们的眼神里,马尔库斯能看到一种地狱看天堂的样子,这反而让他有点不安。
第6营的战士都上了卡车,司机却迟迟没有发动,他从车窗里伸头出来看着马尔库斯他们,“好运吧,各位。”他说。马尔库斯向他点了点头,那司机挥了挥他的军帽,打火离开了。轮胎与雪地的沙沙声渐行渐远。坐在车上的士兵们似乎带着怜悯的眼神看着这些人,在雪地和树林间,掩映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营地,说不清是孤独还是冷寂。

阿克塞尔和佩卡在哨站的木头观察所里面站着,望着远处的林线。
“你去过罗瓦涅米吗?”阿克塞尔问。
“没有,我从出生就在萨拉附近的一个小伐木场生活。”佩卡说。
“如果我能去罗瓦涅米就好了。我的叔叔总说,去了罗瓦涅米,就算是把拉普兰最热闹的地方看了个遍。我嘛......一辈子没去过,”阿克塞尔说,“不过也好,先把拉普兰最冷寂的地方先逛个遍,也许更能体会温暖处的感觉。”
“如果我们能去摩尔曼斯克会更好!在那里还有宏伟的港口和漂亮姑娘,还有好多好多的好酒。”佩卡说,“伟大的芬兰终将把旗帜插到遥远的地方!”
阿克塞尔沉默不语。
“天亮了啊。”佩卡说。
阿克塞尔抬头望去,沉沉的阴云正扑向他们。勉强能感觉到天是亮着的,但是无论他怎么费力地看,都想不到几个小时前营地里的星空那种清澈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他想了又想,这也许还是拉普兰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吧。
“罗瓦涅米会如何呢......”他喃喃道。
这个时候,马尔库斯正在哨站的外面抽烟。他向着萨拉的方向看去,远远的还能看到几点星光,一根烟尽再回首,只看得阴黑的云压了下来,云间还能听到沉闷的轰鸣声。他试着回想萨拉的静谧和营地的星光,可他无论怎么努力地想,他都被面前这严峻的现实压得透不过气。
(未完待续)

请评价一下吧!如果可以,请多多支持(恳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