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学新闻的,果然...”

◼️ 【门槛很低】“全世界都能来掺一脚新传”/“跨考门槛低呗”/“是个人都成自媒体了”/“人人都是新闻记者”/“学艺术的吧”/“不用考数学,随便背背就能380分的专业”/“你新传本来跟什么都沾点边但啥都碰不着”/“新传还要学啊?”/“新传还分内行和外行吗?”/“新传,懂的都懂,高考怎么上来的”/“新传这种水专业没啥好说的”
◼️ 【煽风点火】“学新传的,意满离”/“学新传的一天不发表真知灼见就难受”/“自以为抓到了时代的命脉”/“少发点情绪化的东西吧!烦人”/“虽然我造谣了,虽然我在煽动仇恨,但我是正义的,说的你不就是你”/“你们学新传的不呼吁这个世界就不转了是吧?”/“什么都要同情,什么都要公平,永远热泪盈眶永远被当枪使”/“学了点理论知识就觉得自己是正义使者了”/“新传人脑子不好。”
◼️ 【没有前途】“新传,狗都不读”/“新传毕业能做什么?主持人?”/“新闻理想?笑死人了”/“自以为是的新传人”/“我爸让我新传毕业回老家当婚庆司仪”/“学了新传还不是要进场,进场什么都不会数据都跑不了”/“新传,最万金油也最低薪职业之一”/“学什么不好学了个新传,真没前途。”
◼️ 【没出息的新闻人】“新闻?中国没有新闻”/“记者,这年头谁敢去当记者啊?”/“中国的新闻就是被你们这群煽风点火、流量至上的新闻记者搞坏的”/“再也不相信新闻了”/“什么是喉舌啊”/“学什么?学新闻?没出息!”
◼️ 【来自四面八方】来自秃头所的微博、b站、公众号评论/来自家里的年夜饭饭桌/来自新传考研经验贴的评论/来自新传人自己的微博/来自互联网/来自现实。

📸
02/02/THUR.
一条人文主义的狗,
与消失的新闻业。
@TuTouSuo™️
许知远在今天被很多人讨厌,也被很多人喜欢,他笔下对新闻的理解就和他本人一样:热血、理想、极端、洋溢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天真的浪漫主义——他在《新闻业的怀乡病》里写:
“2001年至2002年间,我正沉浸在啼声初试的喜悦中,在一份年轻的橙色报纸上,以主笔之名对911之后的世界、中国的转型作出喋喋不休、经常不知所云的评论...这既来自于某种自觉,更蕴含着显著的身份期许——我从事的正是有高度历史价值的职业,要比一个银行家、商人、技术专家更为重要。
十六年过去了,这些情绪早已消散:不仅新闻理想主义的特质迅速衰弱,甚至报纸、杂志本身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面对信息的迅速膨胀,记者与编辑都不所适从,它们不仅不再是知识精英与启蒙者,甚至沦为了权力与公众所共同嘲讽的对象。
我们这一代新闻人,不仅无法塑造时代与社会,还会被裹挟在时代的情绪中,疲于奔命,更普遍的缺乏足够的才华和毅力建立内在秩序:一些时刻,我强烈地感到一整代人的失败。”
在一切开始之前/我想先聊聊/我认识的新闻/我以为的新闻/我坚持的新闻/我热爱的新闻/具有极强的主观性/欢迎评论区和我分享你的故事/或者直接参与明天19点开始的秃头所「犬儒主义小酒馆·线上谈话第三期」/分享故事/针砭现实。
⚫️ 学新闻?没什么意义。
即使今天新闻传播被人理解为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行业,人人都能拿着笔写点什么以美名其曰是写报道或做自媒体;即使今天新闻传播专业在跨考中也被很多人误解为是很好考的专业,背一背就好——但于我而言,这些所谓的时代变化下来自学科和行业的“红利”和我毫无关系,我不是因为它不需要考数学而选择它,也不是因为它在就业方面多么万金油而选择考研。我这是很少能非常坚定的表达出来的热爱:我的确非常喜欢这个专业,我也很幸运,过去所学与此刻所为恰恰为自己所热爱。
追溯的话是小学五年级上的课外写作兴趣班,这个班给每个写的不错拿过奖的小朋友发了一本看起来很正规的、红色的「中国小记者证」,而自从我拥有了那本小记者证后,就开始在寒暑假时拉着另一个也拥有这本记者证的同伴,开始了大街小巷的采访活动。
我的第一个采访话题是「为什么要节约用水」。
我和同伴走过了所有一个五年级小学生力所能及的地方:经常跟着父母去的菜市场、菜市场旁边的便利店、家附近的能拍大头贴做美甲的小商品城、公园里下棋的爷爷和遛弯的奶奶——一本小记者证,一个线圈笔记本,一只画着百变小樱的花里胡哨的笔——我们用一周的时间采访、整理、写作文,署上两个人的名字投稿给当地的报纸,在都市报的作文板块被刊登出来,又被我剪下来压在了桌子底下。
我非常确定,想要做一个记者的想法萌生于那一刻:“把散落身边的细碎想法收集并表达,这件事情如此的重要,因为无数细小的声音才会汇成时代的洪流,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有被看到的价值。”(这句话是我当时作文里的原意,我稍改了一些稚嫩的表达)。
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了解到有专门的学校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当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在百度上搜索「哪个学校的新闻专业最好」的时候,一条答案闯入了我的生活:“请问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哪个学校的新闻专业更好?我想学新闻,想在一个自由的地方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哈哈是个比较有野心的人。”这句回答到现在我都能一字不落的复述下来,因为这也恰恰是那个还年幼的我无法表达的个人理想和野心。
还有很多的瞬间:当我在高中看到马航370失联的新闻发布会时,电视里忙碌的记者身影与电视机前拎着书包的高三生形成呼应,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在第一现场,了解情况,传达事实。当我无意间读到一位记者写在网络上的,关于尼泊尔大地震的采访笔记时,我也告诉自己这样的工作是我想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当然,没有一本《看见》是无辜的,没有一期《新闻调查》是无辜的。
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在大人们的谈话中,尤其是在关乎工作、未来的谈话中,我表达了我想要学新闻,专业想要选择新闻系时,大人们的不理解、正襟危坐、和善意的劝说:新闻没有前途、新闻没什么可学的、做不了新闻的、理解一下环境。
“黄金时代过去了,学新闻没什么意义。”
家里有话语权的长辈一锤定音。
甚至一直到今天,我在选择了经济学又最终回到了新闻传播中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也依然坚持:学新闻没什么意义,不信你看看现在的新闻;学新闻没什么意义,你自己不是也体会过账号问题吗?
我的确无力反驳,就像许知远说的:理想主义的特质迅速衰落,现在的新闻被裹挟在时代的情绪里,疲于奔命——纵然过去的我执拗地热爱着新闻,但在很多时候,巨大的无力感也会让思考:
这个时代的新闻,到底在追求什么?
不知道。
⚫️ 新闻理想?是天真的幻想。
我从不吝啬于表达自己的新闻理想,更不会隐藏自己的野心——去年我写:“不甘心这朴素的日常,不甘心这高高的栅栏,不甘心这亮起的红灯和踩下的刹车。”
我也深刻的反思了所有外界的批评:无病呻吟、矫柔造作、非常天真、非常个人化。
批评的没错,因为我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具象地表达「新闻理想」究竟是什么,当然我在这里可以引经据典地说起李普曼、阿兰·德波顿甚至是钱刚老师那句对我影响颇深的:“新闻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事业,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的艰辛劳作”。
但绝大多数时候,我对新闻理想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虚无,尤其是当我试图摒弃掉宏大的公共责任、摆脱无法界定的自由边界,回顾到具体的新闻实践和操作中,回到一字一句的新闻写作和传播中时——我根本无法描述现实中理想是什么。
是什么呢?
不知道。
这也就形成了绝大多数人诟病的:空有新闻理想,只有热血和情绪,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 当记者?不过是颗螺丝钉
很多工作了的朋友和我抱怨自己的工作:完全的内容搬运工、毫无创造力、毫无价值的工作——他最后总结:“坦白来说,我不想在未来称这样的东西叫作品,我也讨厌没有意义的短视频,花30s看他,我不如做两次深呼吸,花一天做出它,我不如再去读一本书。”
而更多的新闻专业毕业的人正在面临着同样的尴尬:或许是一个公众号编辑,或许是创作一条抖音,或许是成为某个账号的内容生产者——在做一方小小的屏幕前,运营着某个可能不起眼的互联网账号:可能是搬运着一些网络上的内容,可能是写着一些无聊的稿件,可能是发布一些没什么人但必须要做的活动宣传,一天又一天。有的人在北上广崭新的写字楼里,运营着背靠大平台的公众号,数据好看留言挺多;有的人在小城市的某个办公室里,艳羡着那些在大厂的新媒体运营,焦虑的完成又一天的推文更新。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机械操作中,一次又一次无聊的复制粘贴里,一天又一天重复的工作里问自己:
啊,做新闻原来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
不可否认,今天的新闻行业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再说任何令人反感的理想主义宣言,赤裸的现实摆在面前,新闻在情绪、流量、权力的裹挟下早已变成了工具,这也是今天社会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对新闻报之以反感甚至唾弃态度的根源:
“姿态很高,却没做什么。”
“理想很好,但只有理想。”
“有情怀是好事,但不太现实。”
“从来都认不清现实的可笑新闻人。”
-未完待续/持续怀疑
这个时代的新闻在追求什么?
新闻理想是什么?
做新闻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酒精/聊天/寻找答案
2023年/秃头所/限时营业
犬儒主义小酒馆
第三期主题「被讨厌的新传人」
2月3日(本周五晚七点)
即将开始!
⛄️
* ᴳᴼᴼᴰ ᴺᴵᴳᴴ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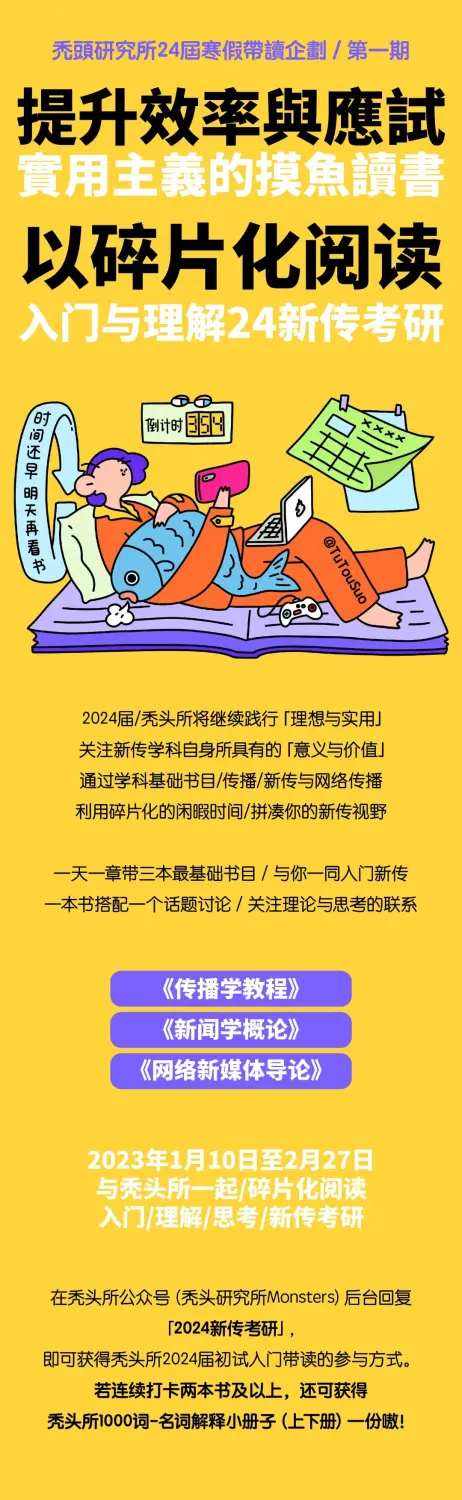
「2024/TuTouSuo」
✧
追逐自我/畅意自由
保持灵魂对Freedom的渴望

「2023/TuTouSuo」
つ♡⊂
将书籍与宇宙一同
随身携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