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放,随时更新】高考语文如何解锁130+,每个高中生都要get的底层逻辑丨

【第一趴是个人听课时的感受 随笔】
希望自己也能毅然追求心中所爱 沉潜十年 任物欲横流 光阴百代 我渴望创造出我的波尔金诺之秋 但即便没有 也依然敞开心扉对现实 因为太阳照常升起 当有情酬旧约 为君谢风流
我看见星月变幻 我听闻滴水石穿 我想象沧海桑田 我期待科技化人
皎皎白驹一时过 庸庸碌碌已成年 曾三分钟热度的拼命努力 曾急功近利的妄想一夜成长 终是在读书籍百本 阅诗篇上千后逐渐明朗:道阻且长 慢一点又何妨
【第二趴 笔记】







最后四轮训练(当年国师所做的):选择3张试卷计算得分率,把自己数据化,列举自我清单
4.10-5.1刷得分率最低的题目,
5.1-5.7回归五三,语文基础手册,补基础知识
5.8-5.30事情很多,周套卷养成,每周三套卷子,每个礼拜选3天在9;00-11.30只干跟语文有关的事,养成生物周期 对自己狠一点可以每天做
6.1-6.6回归真题,不做题,对着答案看试卷,形成答题术语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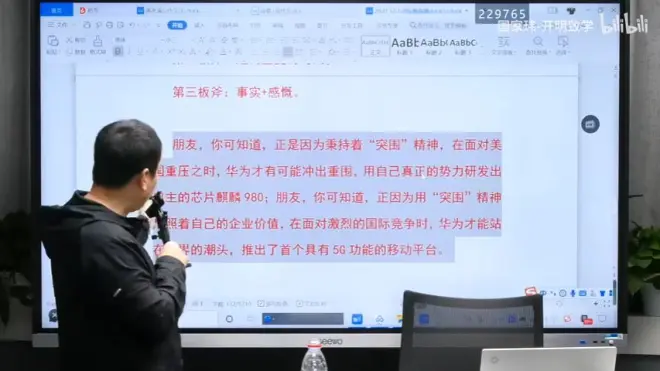













人间。














































萧红墓畔口占 戴望舒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我们准备着 冯至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停电之后 穆旦
太阳最好,但是它下沉了,
拧开电灯,工作照常进行。
我们还以为从此驱走夜,
暗暗感谢我们的文明。
可是突然,黑暗击败一切,
美好的世界从此消失灭踪。
但我点起小小的蜡烛,
把我的室内又照得通明:
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
只是对太阳加倍地憧憬。
次日睁开眼,白日更辉煌,
小小的烛台还摆在桌上。
我细看它,不但耗尽了油,
而且残留的泪挂在两旁:
这是我才想起,原来一夜间,
有许多阵风都要它抵挡。
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开,
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
沉潜十年 钱理群
一、沉潜十年:鲁迅的经验
今天与诸位第一次见面,突然想起了1908——1918年的鲁迅,那是人们通常说的鲁迅的“十年沉默”,其实,就是默默地读了十年书。这就使我想起了诸位,你们从现在开始,至少要读三年书,如果硕博连读,就要读七八年书。那么,鲁迅的读书经验,就可能有点借鉴意义了。
先说鲁迅为什么要沉默读书。这自然要注意到时代的背景,那正是辛亥革命以后。鲁迅说他原来是充满着希望的,但后来“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就意味着,鲁迅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苦闷之中,就只有到书本里去寻找精神出路。这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人们通常是因为苦闷而读书。不知道诸位为什么来读研究生,我猜想,大概多半是要来“寻找出路”吧,或者是生活的出路,或者是精神的出路,更多的两者兼备吧。这是可以理解的。坦白地说,我和诸位这样的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一样,都陷入了世纪末的精神困境。我曾经这样总结自己和我们同代人的精神历程:二十世纪东西方都制造了关于自己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神话,以为是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那时候人们是满怀希望,充满信心的。但到了世纪末,所有的神话都破产了,“东方世界革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都破灭了。于是几乎所有的人,东西方的知识分子都陷入了深刻的怀疑与失望中。于是产生了寻求新的出路的要求。同学们比我年轻,没有我这样的经历,自然也不会有我们这一代这样的怀疑与失望,但你们成长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也就有了自己的理想破灭的苦闷。但从另一方面看,旧的理想的破灭,也就意味着新的追求与探索的开始。这就是我经常和年轻朋友说的,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全球性的呼唤新的思想、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时代。这也是你们这一代新的研究者在二十一世纪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要和诸位着重讨论的是,处在旧的理想破灭、新的理想还未建立这样一个思想的苦闷时期,消极地说,怎样走出苦闷?积极方面,如何为新思想的创造做准备?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如何去做准备?这些,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说不定大家会更感兴趣。不过我所能谈的,仍然是鲁迅的经验,或者说是我对鲁迅经验的理解与发挥。大家姑妄听之吧。
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后,到1918年写出《狂人日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其间的沉默,我更愿意把它称为“沉潜十年”。这“沉潜”两个字极为重要。在自我、时代的苦闷时期,人们最容易陷入浮躁,像无头的苍蝇四处乱撞,习惯于追逐时髦,急于出成果,热衷于炒作、包装等短期行为,因为缺乏定心力而摇摆多变等等,这几乎已经成为近二十年中国学术的积弊了。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其反面: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作为具体的操作,鲁迅在这十年中,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回到古代”,一是“沉入国民”。在我看来,正是这两方面能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二、回到古代
先说“回到古代”。按我的理解,这也就是“回到传统”。对于今天的年轻学者,这传统就不仅是指古代传统,恐怕也要包括近百年已经形成的现代传统(鲁迅本人就是这一现代传统的最主要的代表),而且“回到传统”与继续向东西方其他民族吸取思想资源,也是相辅相成的。这些意见,是近年我反复论说的,这里也不再多说。要着重讨论的是“回到古代”。鲁迅十年读书,主要精力就是辑录古书,特别是在辑校《嵇康集》上下了很大功夫,这是几乎贯穿了鲁迅一生的学术工作。鲁迅还辑录了一部《古小说钩沉》,为他以后研究中国小说史奠定了基础。人们还注意到,鲁迅回到古代,主要是沉湎于魏晋时代,从而形成了他的“魏晋情结”。研究者指出,鲁迅正是带着“魏晋参照与魏晋感受”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打上自己的烙印的。
鲁迅的这一“回到古代”的读书经验,在当今的中国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我们不妨先把话题拉开,说说在你们之前的几代学者的知识结构。像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因为不懂外文,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对西方现代文化甚至处于无知状态,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传统实际是不熟悉的。这些年虽有所弥补,但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比我们年轻的,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活跃的这一代学者,他们中除少数人古代文化的基础较好,大多数也是在八十年代先打下了西学的基础,到八十年代末以后,才来补“中学”的课的。尽管他们以西学的背景(观念、方法等)去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容易地就做出了种种分析与概括,有的甚至形成了某种体系,但就大多数而言,与中国传统文化总有某些隔,他们也未能根本改变古代文化传统修养不够深厚的先天弱点。我们不是进化论的信徒,不能说你们这一代的古代文化造诣就注定超过前两代,如果不加注意,弄不好,很可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但你们毕竟还有时间,有可能来重打基础。如果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尽管也是晚了一些),沉下十年、二十年,从头读起,或许(至少说还有希望)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我这里说的“从头读起”,就是从老老实实地、一本一本地读中国的原典开始,要抛开各种各样的分析、讲解,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塞满你的头脑,而要尽可能地处于真空的状态,像婴儿第一次面对与发现世界一样,直接面对古代原典的白文,自己去感悟其内在的意义与神韵,发现其魅力。
这里,不仅要直接读原典,而且还有一个如何读中国古代原典的问题。请注意,我强调的是感悟,而不是分析。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感悟的文化,而不同于偏于分析的西方文化。要真正进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必须以感悟为基础。我们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发蒙时,老师不做任何讲解,就让学生大声朗读经文,在抑扬顿挫之中,就自然感悟了经文中的某种无法(也无须)言说的神韵;然后再让学生一遍一遍地背诵,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像钉子一样楔入学童几乎空白的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老师再稍做解释,就自然懂了,即使暂时不懂,也已经牢记在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定的阅历,是会不解自通的。这样的教育法,看似不科学,其实是真正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出发的。我今天如此强调学习古代文化中的感悟,也是受到了上述传统教育方式的启发。也许我说得有些神秘,文字上读懂了(尽管这是个前提),如果不能感悟,仍然进入不了传统文化——能不能进入,是要有缘分的。
进入了也还有危险。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进入以后,很容易看得眼花缭乱,迷恋忘返,被其收摄,而失去了自我,成了古人的奴隶。这确实是地狱的门口:要么进不去,进去了却可能出不来。
记得当年闻一多去世以后,郭沫若曾撰文高度赞扬闻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既“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但他同时又十分惋惜地指出,闻先生刚刚钻了出来,正有资格“创造将来”的时候,就牺牲了,这是一个学者“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悲剧。
在这方面,鲁迅或许也是一个榜样:人们不难看出,他在十年沉潜以后,投入新文化运动时,确实已经吃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完整地保留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因此他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时,能够准确地抓住其要害。有的人虽然不赞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态度,但不能不承认鲁迅的具体批评还是有道理的。同时鲁迅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完全融入自己的内在精神之中,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如盐之溶于水而不显痕迹。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对于鲁迅仅是一个基础,一个起点,他更着重的是从传统出发,进行新的创造。尽管他并没有充分地展开这样的创造,这或许也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但这新文化的创造之路确实是鲁迅所开创的。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又“回到古代”时,是不能忘记“创造”这个更为根本的目的的。这里的关键仍然是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这就需要有更强大的自我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力量,更活跃的思想创造力。
我已经说过,我们这一代(甚至两代)学人,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前止了步,现在就看你们这些更年轻的学人,是否能跨过这关键的一步:进去而又出来,深知、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又能做驾驭它的主人,进行更加自由的创造。这正是我首先期待于诸位的。
三、沉入于国民中
现在再说“沉入于国民中”。这是鲁迅十年读书的另一个重点:关注他所生活与生长的土地上的文化,进行地方文化典籍的阅读、整理、研究,辑录了一本《会稽郡故书杂集》。有研究者总结,鲁迅的读书与古籍整理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的,其中存在着两种文化的交织:既有中国文化中的魏晋文化,又有他的故乡浙东的地方文化。因此,鲁迅进入“五四”新文化,不仅有前面说的魏晋情结,还有他的家乡(浙东)情结。鲁迅对地方文化的观照、对地方典籍的阅读,和他童年时候所受的地方民间文化的熏陶,是融合在一起的,表明了他从一开始就和自己脚下的土地,即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乡亲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因此,他在“五四”时期,一开始创作,他的乡亲——闰土、祥林嫂们就一起奔涌于他的笔下。与地方乡土文化、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今天更有极大的启示性。
这个问题近年来似乎很少有人提,但我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是现代中国人,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无论我们具体的研究领域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现实,不能离开我们脚下的土地。
这又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把地方乡土文化、民间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方面,作为我们阅读与研究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还要有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我们当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现实采取亦步亦趋的态度,更不能走以学术为现实具体政治、政策服务的老路。在这些方面,我们这一代有极其沉痛的教训,现在也有人在竭力地鼓吹、鼓励,年轻一代应当警惕与拒绝这样的诱惑。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关怀现实,保持与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人们经常说,学术研究应该有问题意识,但这问题从哪里来,它只能来自于(或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的现实(对现实的理解应是宽泛的,不应狭隘地仅仅限于现实政治)。而对问题的学术性的解决,则有待于不带现实功利性与操作性的,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与学理性的,更为宏观,更加超越,也更带根本性的思考与研究。也就是说,问题是从现实出发的,而思考、研究的心态与视角,则是超越的。真正学术研究正实现于二者的矛盾的张力之中,并随时都有可能落入陷阱:或过于贴近现实而缺少距离感,或脱离现实,失去了学术生命的活力。
强调“沉入国民之中”还有一层意思是,学院里的学术要不断从民间学术、民间思想中去吸取养料。这些年很强调学院派的学术,强调学术的规范化,这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包括在座的诸位)也都是学院里的学人,学院是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这是回避不了也改变不了的现实。但也因此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学院的生存环境的问题,既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正视其必有的负面。学院在学术研究中的优势,这大概是无须论证的,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国家学术研究的重镇。它的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一方面使学院的生活与外部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处于相对宁静与稳定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学术研究所必备的条件,过去曾经随意打破这样的教学、学术秩序,几乎毁灭了学术,这个教训是不能忘记的。但另一方面,长期的封闭,也会使学院失去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丧失(至少是削弱)学术的活力。而学院的体制化,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形成对学术创造力的一种压抑。在这些方面,具有某种野性,即不规范也因此不受约束的民间思想、民间学术,就能够对学院的学术起到补充的作用。学院学术、学院思想应该以民间学术、民间思想作为自己的基础与后盾,二者互相渗透、影响与制约,这是有利于学术整体的健康发展的。而作为学院里的学者,一方面固然要遵守学术的规范,但在我看来,也要多少保留一些不受约束的野性,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最后,还要说一点,沉入国民之中,也可以做更广泛的理解,即一个学者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极为开阔的。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又说,真正的诗人是能够感受天堂的快乐与地狱的苦恼的,因此他的“无边心事”是“连广宇”,连接着无限广大的世界、宇宙的。我想,诗人(作家)如此,学者更应是如此。如果学者的胸襟、视野像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书斋那样狭窄,那就太可悲了。
真正的学者是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他对人与人的世界,对宇宙的生命,以至非生命,都会保持浓厚的兴趣,甚至是孩童般的好奇心。他对人,特别是普通人(所谓“国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最通达的理解。正因为书斋生活相对枯燥,也因为学者因思想的超越而时常咀嚼寂寞与孤独,他对平凡人生中浓浓的人情味就有着本能的向往与挚爱,以至于依恋。张充和曾送给沈从文八个大字:“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学者总是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学者的人与学术之间是有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到沉潜时,首先强调的是人(学者自身)生命的沉潜,然后才是学术的沉潜。我们讲“回到古代”,讲“沉入国民”,最终都要落实到你们自身精神世界的扩展与自由,以及人格的自塑中。我常说,对研究生的培养,最重要的是,通过几年的学习、熏陶,每个人都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至于以后学术成就的高低,取决于主客观的,自己能把握、不能把握的各种条件,是无法强求的。——现在,你们大概已经明白,作为一个导师,我对新一代的研究者的主要期待是什么了吧。那么,我的这篇东拉西扯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1998年9月5日起草于燕北园,10月11日补充;
2014年10月25日略有补充、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