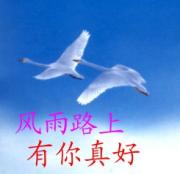于细微中透深邃于细腻中见醇厚
于细微中透深邃 于细腻中见醇厚
杨朔诗化散文的艺术特色
杨朔(1913-1968),山东省蓬莱县人,是我国著名的散文作家。1978年出版《杨朔散文选》,收入优秀作品六十篇。这些抒情散文,大多数为广大读者争相传颂,有些当时就被选作中学语文课本的教材。它们确实代表着杨朔一生文学创作的最突出成就。
杨朔的抒情散文,创作思想是“应该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1)他以诗人的敏感从现实生活中的浪花中,捕捉时代精神的旋律,一方面注重描写新生活、新时代的绚丽色彩,另一方面又注重描写普通劳动者真诚、朴素的感情,从他们身上富有哲理性的发掘至真至美的诗意——“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2)
杨朔具有浓重的诗人气质,“善于在一片奇景,一幅花草的素描里,再现当前的生活。”(3)杨朔明确提出了诗化散文的艺术主张,“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4),正因为他在自己创作实践中孜孜以求“诗”的目标和审美理想,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
以下尝试谈谈杨朔如诗散文的艺术风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和人相联系,被美好的思想感情所照亮。
“杨朔的散文是新时代、新生活的赞歌,也是普通劳动者的赞歌”(5),善于从平凡的劳动者身上发掘出诗意美,描写普通劳动者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执着精神和高尚情操,以革命者的情怀展示中华民族内在的晶莹剔透的心灵。散文虽有的状物,有的绘景,都少不了人的描写,都与人相联系。杨朔写人,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着意于以白描手法勾画人物的音容笑貌、神情语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让人物的思想感情,像破云而出的阳光照亮了文章所状之物,所绘之景,照得全文通体璀璨夺目;又如皎洁的月光,給景物洒上了一层朦胧而透明的华辉,让人强烈感受到一种含蓄蕴藉的诗意美。如《荔枝蜜》里,养蜂员老梁领我参观“养蜂大厦”,对人物进行了语言描写:
老梁赞叹似的轻轻说:“你瞧这群东西,多听话!”
老梁说:“能割几十斤,蜜蜂这东西,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有限,每回割蜜,留下一点点,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这里老梁是在赞叹蜜蜂,其实也是在赞美“在水田里,辛勤的分秧插秧”的农民,在赞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奉献精神。如此前文“每逢看见,感情上疙疙瘩瘩的”小蜜蜂,“调上半杯一喝,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的味儿”的荔枝蜜都漾溢出不平凡的耐人寻味的意味。
“对散文写人,有的比作素描:寥寥数笔,活灵活现;有的比作淡画:轻轻勾画,呼之欲出;有的比做雕塑:三刀两斧,神形毕肖。总之,这些比喻中都包含一个“粗”字的意思”。“确实,粗字是散文写人的特点。”(6)但是大凡优秀的散文作者在写人时,粗中有细,而且非常细,细到入木三分。杨朔写人就注意了粗中有细,如《雪浪花》里:
“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的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胡子。瞧他眉目神气,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
运用比喻修辞,刻画了老渔民的朴实、豪爽的性格,犹如电影的慢动作,缓缓的尽情展现在读者面前,又仿佛把一个细胞,置于显微镜下,加以放大,清楚地告诉读者。
再如《樱花雨》作者描写了在箱根遇到的一位腼腆秀美、柔弱胆怯的下女君子姑娘,起初描写了君子犹如一只惊魂不定、形单影只的柔弱小鸟。作者哀其不幸、怜其不争,带着怅惘的疑团将要离去。这时忽然间停电,宣告罢工斗争已正式开始,她忽而判若两人,柔和的眼睛里“有两点火花跳出来”,由此作者看到了饱受摧残的樱花,“也能舒开笑脸”,能忍受风寒,“更能冲风冒雨”,这才是日本人民真正的性格。在关键之处,作者通过细致描写,把君子的本质特征展现出来,表现了人物的美好追求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从君子那对柔和的眼睛里跳出来的“两点火花”,照亮了“风雨中开放的樱花”,赋予其奇特炫目的光彩。
二、设眼点睛,化实为虚,曲中见奇。
散文,是常常取材日常琐事,着笔于事物细处,却偏偏能让人从平凡之中辨出新异滋味,在细微之处窥见宏旨精义,做到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7)杨朔的散文构思就“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抓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生发联想和想象,洞隐烛微,见微知著,作品思想得到寓大于小,寓远于近的艺术表现,因此具有诗的视角和诗的容量。”(8)这归功于作者体物入微,善于运用“画眼睛”的艺术。体物入微,并非是触及事物的细微末节,而是对于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繁杂错综深邃微妙联系的摸索和发现,古人论文云:“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9)要做到即物明理、即事寓情,就要找到理与物、情与事的联系,对这一联系揭示的愈精愈巧,则文章的意境也就愈深愈新。
意境的构成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形象,杨朔的散文都注意刻画、抒写一个主体形象,凭着它,营构意境的轮廓,凭着它倾注作者内衷的诗情,从而因小见大,以少胜多,以有限展示无限,以集中凝练的形象传达丰富深刻的思想。《金字塔夜月》是以人面狮身斯芬克斯石像脸上的“神秘表情”作为眼,来构成意境的内核。开头部分叙写夜色沉沉中金字塔向人们展示的魅力,引起作者的茫茫情思,为表现和揭示斯芬克斯的神秘表情,定下了特殊的格调。第二部分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为表现和揭示神秘表情投下鲜明的时代色彩。第三部分在渲染月亮露面,金字塔远近一片静的氛围后,才正面描写斯芬克斯的形象,脸上“永远是个猜不透的谜”的表情,又借埃及朋友的嘴,老看守坚贞如一的气节,从思想上对神秘表情写照传神,最后部分借老看守的话揭破谜底:斯芬克斯“面向东方,五千年了,天天期待着日出”。这篇散文,作者把握住神秘表情这个眼点,作为意境构图的支架,对各种风景画、风俗画和人物画,进行了由远及近,抽丝剥茧的有机安排,借这个形象抒写了埃及民族从古至今五千年来不屈不挠、英勇悲壮的历史。
可见眼往往是散文诗情吐发的依据,又是诗情的泉口,散文画眼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艺术功能。画眼必须点睛,点睛是散文画眼睛的最后一笔,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笔,是对眼本身的一种艺术阐述,点睛是散文意境之跌宕,主题之开掘,诗情之升华的必然,有如夜空中一道闪电,恰是出墙绽放的一朵红杏,点燃了读者的眼睛。如《雪浪花》结尾部分描写老泰山退场的画面: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彤彤的。老人.......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
这样便把自然美精神美抒情美浑然一体涵容在一幅图画里,“黄昏颂”的主题因而显得含蓄悠远、诗意隽永。
有的作品作者不是以画点睛,而是以隐而不露诙谐幽默的话语启迪读者思索回味,去领略作品的题旨。如《野茫茫》:
“前后在野兽世界里转了五个小时,我的神智弄得有些奇怪,看见耕地的水牛,疑心是野牛,看见农家门口卧着的狗,也当是野狗——仿佛什么都是野的。对面开来一辆汽车,里头坐着几个军人,放肆的高声谈笑,一听就知道是美国人。奇怪,我也觉得他们是野兽。”
三、题材细微而诗意醇厚,语句寻常而蕴藉婉丽。
读一篇好的散文,常常是如啜香茗,余香满口。这来自思想的精粹、意境的隽永,同时也来自作品的语言美。杨朔并不以为散文可以任意放肆笔墨,而是象写诗那样,用诗的比兴手法,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以创造诗的象征比附境界;再三剪裁,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以结构的缜密精美,着力表现抒情诗般的思想内容。杨朔就说过:
“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新鲜的意境,思想感情耐人寻味,而结构上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10)
杨朔的散文,许多题目就有诗意,如《金字塔夜月》、《晚潮急》、《野茫茫》、《秋风萧瑟》等。但题目不过对作品作了诗意的概括,也加强了整个作品的诗意,但根本还是作品内容。“作者在所有的日常琐事中,感着无上的甘露味。”(11)善于从生活矿山中采掘具有诗意的矿石,用美好的思想感情去冶炼它,发掘出平凡中蕴含的不平凡的意义,灌注灼热的革命感情,作品具有浓烈的诗的质素。《茶花赋》先描写了西山华亭寺的花事,描写了一幅“春深似海”的画面,然后笔锋一转,赞美养花人的勤劳质朴和用花美化生活的高尚心灵,字里行间流漾着花与生活、美与创造之间的哲理情思。然后又拓开一笔,渲染茶花中间一群孩子甜蜜的笑脸,叽叽喳喳的笑语。最后总收一笔画龙点睛:“用最浓最艳的朱红花一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可以象征祖国的面貌?”,使意境的展示虚实相生、峰回路转,思想的揭示步步开拓,曲径通幽,因而形成了富有诗意的意境。
状物写景极尽自然的风采,如写桂林山石,“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累累垂垂的石乳一直浸到江水里去,像莲花,像海棠叶儿,像一挂一挂的葡萄,也像仙人骑鹤、乐手吹箫……”。且写景,既有自然美,又成为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画山绣水》,作者不惜工笔去描绘桂林山水,将古老的传说、山水的秀美、崭新的生活自然相联系,将自然美升华为生活美艺术美,犹如无韵之《离骚》。
杨朔散文的语言技巧娴熟,很注意选词用字的精炼,表现为清新俊逸、蕴藉婉丽的风格。语言简洁而潇洒,回旋盘绕,如丝如缕,如山间清泉,潺潺而淌,一句连一句,一节跟一节,而又句中无余字,篇中无剩言,时与山石相击,则锵然有声,悦耳动听;朴素而优美,离不开作者的精心加工,将“艺术的匠心”藏于“自然的气势底下”,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运用他久经磨砺的斧刀,进行雕刻、錾凿。虽“造语平实,却光彩动人;稍事修饰,亦不失于夸饰堆砌”(12);自然中透着情韵,作者常常将自己置身于万物之中,同宇宙万物神晤默契,故其感受往往突破一般超乎常人,更加深细而新奇。要将这种感受写出来,自然要推敲出一些带有浓烈的情调、气氛和作者个性色彩的字句来。如:
“久去异国他乡,有时又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点,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
身在异域,怀念祖国,感情既是饱满,又是急切的。但是,这种感情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不是一泻无余的,而是曲折的委婉的。“有时难免”说的很婉转。“怀念极了”表示感情已经饱和,蓄积的潮水该出现巨浪喷雪的壮观吧。可是作者却不,潮水要喷泻,再加一道闸门拦住:“我也曾想……”说的幽婉回荡,让急奔的浪头产生漩涡、微漾。作者产生出画画的愿望,这样的情韵使这篇散文情深款款、情意绵绵,出现了悠然的长长流水,语言节奏一转再转、一折再折,语言气势就像上海豫园的九曲桥,翰旋回环;像苏州的园林,曲径通幽。
杨朔的散文,做到了文思情趣的统一,起笔自然,似乎漫不经心,却富有生活气息;行文曲径通幽,引人入胜;结尾深含寓意,使全篇浑然一体。“一般采用曲径通幽,卒章显志的园林式结构,于云遮雾障中峰回路转,层层迭迭,变化多端,显得缜密精巧。”(13)从单纯中求复杂,从复杂中求简练,使艺术结构与创造意境、抒写诗情很好的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属于他个人的清新俊逸,蕴藉婉丽的艺术风格。
但是杨朔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品在构思上存在着固定的模式,爱用“托物言志”,惯用比兴和卒章显志的手法,因刻意求诗,过于追求散文结构上的精致,反而失之雕琢,在艺术表现上留有雷同化的倾向和求工的斧迹。然而“他的散文总是那么刻意地追求美、构造美并且热情地歌颂美,总是那么执着地去寻求文字的诗情画意,渴求做到形短意长、言微旨远”(14),不少作品至今仍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在文坛上赢得很高的声誉。
引注:
(1)杨朔:《海市》小序,作家出版1960年版,第一页
(2)杨朔:《茶花赋》
(3)周立波:《散文特写选(1959-1961)序言》
(4)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5)《中国当代文学》第二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343页
(6)《散文的艺术》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年76页
(7)郁达夫语
(8)《中国现代文学史》吴宏聪、范伯群主编 1991年版 539页
(9)清刘大櫆《论文偶记》
(10)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第147页
(11)转引自《小品文研究》
(12)《散文的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30页
(13)《中国现代文学史》吴宏聪、范伯群主编541页
(1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下册钱谷融、吴宏聪主编419页
参考书目:
1、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钱谷融、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下册
3、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
4、钱谷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下卷 华东师大出版社
5、《散文的艺术》 百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