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到读者——读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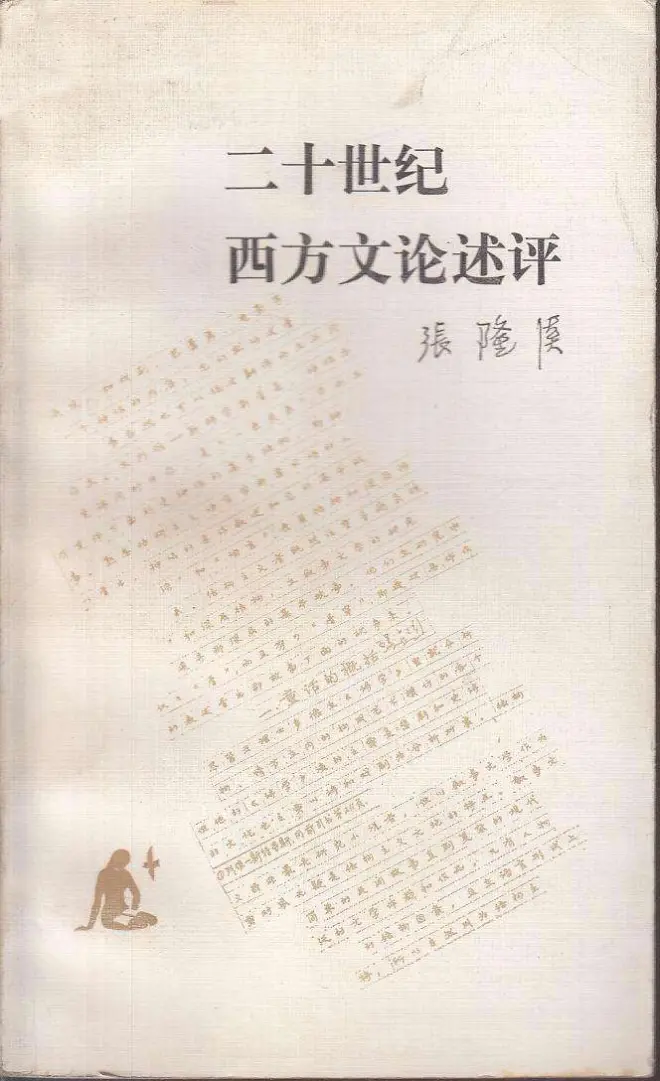
张隆溪先生是世界级华裔学术大师之一,北京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曾受到过著名文学家钱锺书先生的提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是一本极薄的小册子,但在张隆溪先生考究凝练的笔法之下拥有了十分广博的容量,将20世纪的主要流派与发展脉络进行了有效的梳理与概括,同时还不忘联结中国传统文论。此书可做文学理论的窥天之管,测海之蠡。
本文将概述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概况,并着重关注其发展的重要趋向,即从以作者为中心逐渐转向以读者为中心。本文将指出这种现象,并试图探讨其背后的思想原因,以及这种发展趋向对今后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20世纪可以说是批评的时代。”张隆溪先生在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里这样说道。在20世纪西方文论兴起之前,19世纪可以说是以创作为中心的:作家与诗人对文学批评嗤之以鼻,而实证主义的文论则强调研究作者的生平和生活背景,认为这是了解作品的前提。“20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总趋势,那就是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作品本身和对作品的接受为中心。”
一、 从作者到作品
19世纪注重考查作者的生平及其对作者创作的影响,了解作者是进入文本的前提。但20世纪的文论则开始绕开作者进行批评。首先是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导向的文学批评理论,他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文学创作,试图得到一个对文学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原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将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无意识本能,超我是社会道德的制约,而自我是本我与超我相斗争的场域。因此,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来源于本我与自我的冲突,所有文学活动都是情感在压抑过后获得升华而形成的产物,并且弗洛伊德将这些概念的解释归结到性欲(libido)的驱动力。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分析派文论,就旨在各个文学作品中寻找性欲的象征痕迹,进而用精神分析去解释它。这种做法自然已经是脱离作者本意的了:从研究作者的主观能动创作变成了研究作者的无意识。

紧随其后的是英美新批评文论,其兴起直接来源于对实证主义理论的质疑。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理查兹着眼于文学作品在读者心理上产生的效果,认为一部作品只要总的效果统一连贯,就具有“内在的必然性”(internal necessity),就是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具有艺术的真实。另一位新批评理论先驱艾略特则认为,“艺术的情感是非个人的”,诗人在创作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情感的“客观关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用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艾略特和理查兹的理论奠定了新批评的基础,随后形成的把作品看成独立存在的实体的 “文学本体论”论调,成为新批评理论的最根本特点,正如艾略特所说:“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都不是指向诗人,而是指向诗。”[1]

以维柯《新科学》中的神话隐喻思维为起点,弗雷泽《金枝》中神话对季节更替的模仿理论为发展,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概念的提出为中心,原型批评文论就此兴起。作为原型批评集大成者的弗莱,将文学视作是“移位的神话”,文学的发展演变也遵循季节的更替,并在具体批评实践的过程中打破作品之间的界限,去考察一类作品的普遍性。文学的程式和典型的考查,更是将作者推远了。

在20世纪的东欧则兴起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该理论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笼统的文学,而应该是“文学性”,亦即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的东西。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陌生化”理论,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陌生化我们对周遭事物感觉这一过程,从而唤醒我们在惯性动作中失去的感受和知觉。“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只知道事物。”[2]而俄国形式主义的旗手雅各布森与捷克的布拉格学派一起,着手从分析语言的各类功能入手,这直接启导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对文学作品具体语言的考查分析,使得作品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扩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向趋势,作者开始失势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作品本身、作品之间以及作品内在肌质的深入研究。这也为后续的读者地位上升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二、作者已死,读者出世
20世纪西方文论最重要的一支当属结构主义理论,它具有极强的现代性,同时蕴含着后现代的种子,开辟了广阔的文学研究领域。这个过程也是作者逐渐退出,读者地位逐渐上升的过程。
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衍生出的结构主义文论,着重探讨着个别的“言语”(speech)与整个“语言”(language)系统之间的关系。语言学中的“二项对立”原则被应用于文学研究当中,从时序上的横向、同义词上的纵向构成的言语网络中见出文学的意义,这是具体实践时的操作;在整体的思想把握上,结构主义倾向于找到“故事背后的故事”,从具体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中(“言语”)中找到一个具有概括意义的共性故事(“语言”)。这种具有简化倾向的结构主义文论,越发地不依靠作者来引导读者了。

之后我们便迎来了后结构主义文论,由哲学家德里达提出的关于符号的论证,将二项对立原则的深层意涵挖掘了出来:被选择的词实际上是带有未被选择的词的痕迹的。从这一点出发,德里达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没有文本是真正独创的,所有的文本都必然是“互文”(intertext)。结构主义者力求描述出一个结构内核,而后结构主义者则否定其存在。否定作品有不变的内核也就否定了作品的封闭性。于是乎,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就像当年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一样,他宣称“作者已经死去!”互文性概念推翻了作者的权威,阐释文本意义的大门向读者敞开了。

在作者的“上帝”身份被推翻之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兴起了。阐释学有着很长的历史传统,几乎都没有逃过“阐释的循环”:即先定的阐释观念主宰了阐释活动,而被主宰的阐释活动用来证明这一先定的阐释观念。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自圆其说,阐释学没有获得真正的地位。直到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哲学地角度出发,将阐释学从认识论转移到本体论上,“理解的循环并不是一个任何种类的认识都可以在其中运行的圆,而是定在本身存在的先结构的表现”,认识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循环,所以“具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摆脱这种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参与这循环”。[3]接受美学在阐释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作品的接受有两极,一极是作者的本文,一极是读者将其具体化的过程。文学不再具有惟一的理解,本文的具体化和读者作用的实现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文学从读者接受的过程来讲大有可为。

三、转向趋势的背后与前景
20世纪是理性的世纪、科学的世纪,在启蒙运动和进化论的发现之后,上帝的权威被逐渐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思考的力量。20世纪西方文论很多都是建立在所谓的“科学研究”思维之上的,依靠大量的实验取证和统计分类,对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进行概念性的描述,试图把握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得到一种文学的“真理”。但这似乎有将“真理”变成了新的“上帝”,对普遍规律的盲目崇拜让无数文论学者前仆后继,同时也激起了更多人的否定,于是乎学派更迭之快、理论否定性之强都是前所未见的。
西方文学理论的转向是对读者、学者的思想解放,让每一个研究者的思考都得以获得重要的地位,文学理论获得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之后,我们见到了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等等不同角度的文学理论;同时文学理论所涉及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它逐渐和哲学、符号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进行交叉与互动,焕发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带有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离散型思维,并且蕴含着较强的相对主义倾向。后结构主义对作者和作品意义的“消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任何一种角度都可以被提到较高的位置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思考这种理论的价值与意义。理论的碎片化趋向固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碎片化所导致的喧哗驳杂,反抗事物及认识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主张碎片就是一切,否决系统整一的理论追求,推崇学派与方法的孤立。新的学说一旦形成,便自绝于其他任何理论,声称与他人理论没有任何联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在愈发广阔的文学研究前景到来之时,我们不应该只顾着冲在前沿垦荒开辟,还得追求一种更具有统一性的理论来引导人们的思考,避免陷入后现代思潮的喧嚣狂欢。[i]
————————————————————————
[1]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圣林集》。
[2]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i] 参考文献:
(1)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2)张江《关于西方文论分期问题的讨论——当代西方文论基本定位》,《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