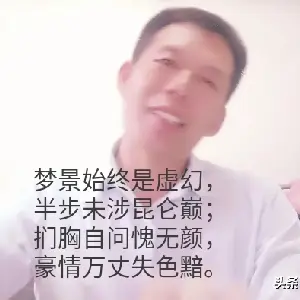一场山洪曝露了大宋第一大表演系诗人——苏轼(一)
#写诗鬼才#一场山洪曝露了大宋第一大表演系诗人——苏轼(一)
在听此文之前,我先告之您,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假相,真相在哪里?在实践中,此文是我经过三年打磨才得到的一些观点,大概要花上十七分钟。希望听了此文,让您有些新的思考。
大宋的诗人表演系的多一些,他们大多都是偷大唐诗人的诗文,还美名其曰为集句,真是笑死个人。而第一大表演系诗人当属苏轼莫属。
在以前读苏轼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我一直认为他写的很好。您看他怎么写的: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另有小序: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春雨如丝,兰芽初发,溪流清清,松翠沙净。多好的意境呀。
据史料记载,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七月被押,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达贬所黄州。至元丰七(1084)年,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 在黄州应该呆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夏,大雨,伊、洛间民被溺者十五六。(大雨造成50-60%人口被淹)1084年,“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大名……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
明白了此段数据,再回头看他写的诗文,才明白,写的好并不见得做的好,才知道完全不是某些人讲的那么回事,因为上阙的山下兰芽短浸溪,写的是下面的方位,松间沙路净无泥写的是上面的方位,而他本人正好处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分明当时正是他被贬黄州,萧萧暮雨子规啼即表明他想家。再看下阙,谁道人生再无少?很明显想到了那个盛唐时期大文学家顾况口中由白居不易到居即易矣,很显然他感到生活的不易。可是不易又能如何,又不能去死,只得忍气苟且,只好自慰自己,然后说,门前流水尚能西,自己安慰自己讲,休将白发唱黄鸡。说明他此时还不服气,想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会整他。一句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表明了他还寄望于东山再起,不认输,不服气。他曾写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自然也就明白即便门前流水向西流去,但最终的归途还是东海。此刻的他已经被折腾的乱了分寸,不是胡言乱语,就是为了安慰自己发奋图强,只是他心术不正,除了兄弟苏辙及那个痴念旧情的章惇能帮到他,再也没有朋友会帮他。
纵观全文细细品味,不难发现这写的是刚刚下了一场大雨过后引发的山洪,因而不是世人普遍所讲的元丰五年(1082年)春,因为春天大多是没有山洪的,而是写在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夏,要知道大多夏季子规才会啼叫,才会有山洪暴发的大灾难。之所以用了一个“浸”字,正好暗示了山洪的暴发。山洪多大呢?淹没了山下游的兰溪镇,看似蕲水只是刚刚漫到清泉寺门前。由于当地东北高西南低的地势原因,东边的寺庙高,洪水来,也没事,可是处在西边下游的百姓们就惨了,但是他并不明写,只是暗写,后面的子规啼正好说明了他不敢明写,为什么不敢明写呢?
看看他的《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现在明白吧,他当时只是个水曹郎,管理河道的官吏。可是发了大水,百姓们受了水灾,他又怕受过训责,不敢把实情上报朝庭,为升迁只好写诗报喜不报忧,自己也觉得真够无耻的。所以说只是惭愧没干什么人事,还浪费百姓们的血汗钱白吃白喝。
苏轼之所以会被贬黄州后又被提拔朝中,除了苏辙及章惇痴念旧情的相助,还得益他报喜不报忧的操作,元丰七年,汝州山洪暴发,朝庭看他在黄州的成绩,错以为他治水有功,心想,就派他去汝州治水吧,毕竟,他当年在徐州就有治水经验,也该他庆幸,汝州的水小,一下就给他治着了,有苏辙及章惇帮忙,他又向王安石认过了错误,自然很快又被调回了朝中。
不得不提的是,在乌台诗案中,章惇为挽救苏轼免死,在皇上面前仗义执言,顶撞时相王珪,可谓是“真君子”;而至绍圣年间,章惇持续贬谪苏轼,欲置其死于流放之途,可谓是“真小人”。
曾是苏轼最亲密友人的章惇,为何却成了逼害苏轼的最凶恶的敌人?“真君子”与“真小人”,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汇成一体?究竟是何因素,触发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翻转?
如果用一句话回答:苏轼在处理与章惇关系上,犯了不可宽宥的低级错误!
且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元丰八年(1085年)初,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哲宗年幼,接掌皇权的是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反变法的旧党人士渐复起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马光和苏氏兄弟。新党重臣章惇初期在朝,由通议大夫、门下侍郎,改知枢密院。新、旧两派人士,围绕新法的存、废展开激烈交锋。司马光抱老病之躯,欲尽废新法。朝堂上的唇枪舌剑,司马光显然不是章惇的对手。章惇气盛且有辩才,嬉笑怒骂、荤素搭配、语锋四射,常常让司马光处于窘态,乃至于请苏轼传话给章惇,劝其勿当众羞辱他。由此也可见,此时苏、章的友好关系尚未破裂。
神宗去世后,新、旧党交锋胜负一度处于胶着状态,但司马光的背后是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因此司马光一进入中枢,一道道废除新法的诏令接连下达。变法派人士纷纷被贬黜离京。章惇也是被旧党围攻、弹劾的主要攻击目标。在诸多弹劾奏章中,用语皆很刻薄、恶毒。章惇被列为罪大恶极的“三奸”和“四凶”之一。对此,也许在章惇的意料之中,出乎他意料的是苏氏兄弟也加入了对他的“恶攻”行列中。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十八日,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则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于其口,而行于其手,小有龃龉,贻患四方。势之必然,法不可缓。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枢府,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惇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苏辙在此奏章中,指斥章惇在变更推行免疫法问题上,居心叵测,“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明确地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职,“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苏辙乞罢章惇,有政治理念、党派不同的因素,但如果仅仅因此而翻脸不认人,对其兄密友,且有恩于苏轼的章惇拔刀相向,是否太无情无义了?在章惇看来,握着刀把的手不仅仅是苏辙,也有苏轼。众皆所知,苏氏兄弟的关系亲密如穿“连裆裤”,苏辙在弹劾章惇前,按常理该与其兄通气。苏辙的翻脸无情,也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即便苏辙上章前,苏轼不知,但在苏辙上章后,也未见苏轼有回护章惇的任何示好言行,等于默认苏辙的攻击是对的。
司马光变更免役法产生弊端,“苏辙不弹劾司马光,却归咎于章惇”,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惇自感愤恨不平”。苏辙的奏章“夸大章惇恶行,力加挞伐,目的只有一个:将章惇逐出朝廷。”
苏辙弹劾给了章惇致命一击,五天后章惇被贬知汝州,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闲人。用章惇语自道是:“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令人感到尤为不解的是,在章惇已出知汝州后,苏轼又对章惇补插一刀。在上奏的《缴进沈起词头状》中,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
苏轼此“状”中阐述的理念,与司马光处理边防的“苟且”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司马光主张宁可割让土地给邻国,以此换取边境的和平。这种以肉饲虎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而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在此事上,苏轼随官位的变化而“前恭后倨”,评价截然相反,文名显赫如日月光耀天地的苏轼先生,难道在做人上也可以如此不堪吗?更何况面对的是曾经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仗义执言的恩人。苏轼先生难道此时,已将在黄州写给“章七”的信札忘得一干二净?章惇不再是他给予高评的“奇伟绝世”的章惇了?说此时的苏轼“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算不算过分?士人皆知苏轼是有情有义的“真君子”,此时为何成了无情无义的“真小人”?
政坛风光常常不可持续。常言:“一朝君子一朝臣。”苏轼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位极人臣,成了他晚年凄惨命运的主导者。
苏轼在早年与章惇交往中,就深知章惇是能“拼命”、能“杀人”的狠角色。昨天章惇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一翻脸,章惇也可以对你两肋插刀。
你不仁莫怪我不义,由你做初一就不兴我做十五了么!一切的果皆有一个因在起作用。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要让苏轼死于颠踬之途的为何是章惇。而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中,其实也有他自己。呜呼,愚夫为先贤悲泣唏嘘时,也忍不住时时要捶击自己的胸膛。
苏二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小人一个,风光时怪牛逼,倒霉时难得有个章惇把他当作朋友帮他,帮了他之后他却反咬人家一口,导致人家章惇被贬八年,可人家章惇并没和他计较,一直在暗中保他不死,你在海南有吃有喝的消停些不好吗?没想倒他却暗中使小动作,又把人家给整了下去,人家也就保不了他了,他以为进京就能当大官呢?宰相之位不知有多少人在暗中去争了,那些人不害死他才怪呢!有章惇在,多少还念点旧情,保他不死,章惇不在高位了,谁还会保他呢?唉!自己稀哩糊涂的咋死的都没弄明白,真是个可怜又可恨的阴险之人。
苏二缺最大的错误是不该恩将仇报,更何况为了家族的私利去诬陷章惇,他兄弟二人以为很聪明,只是他们的聪明用错了地方了,要知道章家人可不是光耍嘴的,人家可是手中有兵的,人家家族可是有军功的,他们那点小聪明又怎斗得过章家人呢?章惇在高位时,可以念及旧情保其不死,可苏二缺悟不透呀!非得搞小动作把章惇搞下去,章惇下去了,也注定了苏二缺悲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