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帝国(第三期)
阿拉伯医学
(一)自7世纪起至其后的一二百年间阿拉伯人初步建立起一个西起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大唐西部边境与印度信德地区的横跨亚、非、欧的世界性帝国——阿拉伯帝国,这一帝国的文明达到很高的水平,其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技术及文化成就。即使在帝国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保持领先地位,直至文艺复兴后世界科学中心才由那里转往欧洲。帝国在科学文化上持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态度,从而大大推动那个时代的医学进步和发展。阿拉伯帝国的医学成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与其它文明不同的是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成就与伊斯兰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伊斯兰产生之前的漫长岁月中阿拉伯人以及帝国内其他一些后来皈依伊斯兰的民族完全笼罩在古埃及、印度、希腊、罗马与波斯文明的阴影之中。随着阿拉伯人版图与活动范围的扩张,许多民族如波斯人成为信奉由阿拉伯人率先传播的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由于践行伊斯兰所倡导的真主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因此帝国的阿拉伯人及其他民族在科学文化上持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态度,从而大大推动那个时代的科学进步和发展。拉齐(865~925年)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与哲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他学识深邃而广泛,一生写作200多部书,尤以医学(与化学)方面的著作影响巨大。拉齐曾先后担任雷伊(位于伊朗德黑兰附近)和巴格达医院院长,并从事学术著述,被誉为“阿拉伯的盖伦”、“穆斯林医学之父”。

(二)拉齐在医学上广泛吸收希腊、印度、波斯、阿拉伯(甚至中国)的医学成果,并且创立新的医疗体系与方法,他尤其在外科学(例如疝气、肾与膀胱结石、痔疮、关节疾病等)、儿科学(例如小儿痢疾)、传染病及疑难杂症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理论知识。他是外科串线法、丝线止血和内科精神治疗法的发明者,也是首创外科缝合的肠线及用酒精“消毒”的医学家,还是世界上早期准确描述并鉴别天花与麻疹者(中国人认为中国的葛洪是最早描述天花症状的,在拉齐之前也有一位阿拉伯帝国的学者介绍过天花与麻疹,但拉齐的论述更为后人所了解),并且将它们归入儿科疾病范畴。拉齐注意到一种疾病出现的面部浮肿和卡他症状(如打喷嚏、流清涕)与玫瑰花生长及开放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他第一个指出所谓的花粉热就是缘于这种玫瑰花的“芳香”。拉齐的代表作《曼苏尔医书》是医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他于903年把《曼苏尔医书》捐献给萨曼尼德的王子兼雷伊地区长官曼苏尔。《医学集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著作,作者花费15年的时间完成此书。《医学集成》主要讲述的是疾病、疾病进展与治疗效果,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保存有一部《医学集成》的阿拉伯语手抄本,它是在1094年由一位佚名抄写人抄写的,也是该馆最古老的医学藏书。《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分别于1187年与1279年在西班牙深受穆斯林文化影响的历史名城托莱多与法国的安茹被译成拉丁语而在欧洲广泛传播,并且随即取代盖伦(130~200年)的医书。

(三)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被多次翻印,并且由当时著名医学家加以注解。此外他还著有《医学入门》、《医学止境》、《精神病学》、《天花与麻疹》、《药物学》、《盖伦医学书的疑点和矛盾》等。拉齐确信他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一定会被比他卓越的思想超越,在他看来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因为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伊本·西那的医学成就主要体现于一部极其著名的百万字医学百科全书——《医典》,他在《医典》的开篇中说:“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告诉人们关于机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人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珍惜健康,并且帮助人们在失去健康的时候恢复健康。”《医典》一书全面而系统,全书包括五部分,分别讲述医学总论、药物学、人体疾病各论及全身性疾病等内容。感染性疾病曾经一直是人类疾病的第一位死亡原因,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类疾病是由病原体例如致病性细菌、真菌与病毒等引起的。伊本·西那提出人本身以外的因素在引发疾病方面的作用,首先发现“原体”可以是产生疾病的原因,指出肺结核就属于此类疾病,天花和麻疹也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原体”所致,而且还强调“消毒”的重要性。他发现水与土壤可以是传播致病物质的媒介,伊本·西那不但认识到钩虫病是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并能够做出准确的诊断。伊本·西那对医学的造诣是广泛而深入的,他主张外科医生应该在早期阶段治疗恶性肿瘤,以确保对所有病变组织加以切除。

(四)伊本·西那在著作里强调膳食营养的重要意义,提出气候和环境与疾病有关的观点。他研究过心脏瓣膜,发现主动脉有三个瓣膜,瓣膜的张开与关闭配合心脏的收缩与舒张,从而维持血液的流出与流入。伊本·西那描述和记录有关心脏病药物的提炼以及皮肤病、性病、神经病(例如脑膜炎)与精神疾病等病症,他还能够将纵膈炎与胸膜炎相鉴别。他也介绍用烧灼治疯狗咬伤、针刺放血与竹筒灌肠以及音乐等疗法,此外中国医学的诊脉也被收入到其著作之中。伊本·西那主张在正式推广使用一种新药之前首先应该进行动物与r体实验,从而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医典》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起直至17世纪的数百年间始终被欧洲的医学院校用作医学教科书,仅在15世纪的最后30年内这部著作就被用拉丁文出版过15个版次,它对西方医学的影响胜过任何一部医学著作。著名医学教育家奥斯勒(1849~1919年)博士对《医典》的评价是“被当作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它任何著作都要长”,《医典》是现代医学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其实伊本·西那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他一生写了450部著作,它们不仅是关于医学的,还有专门论述哲学、心理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逻辑学与音乐等学科。其中传世的有240部左右(关于哲学与医学的分别为150部与40部),例如影响力仅次于《医典》的《治疗论》一书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五)扎哈拉维(936~1013年)是出生在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的著名医学家,享有“外科学之父”的赞誉,其祖先来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安萨尔部落。扎哈拉维的《医学手册》是一部集其数十年医学知识与经验的著作,包括30篇的内容,涵盖大量临床问题,适用于执业医生与医学生。这部著作附有历史上最早的外科器械插图与文字说明,而且数量相当丰富(200幅左右),这些精致的插图(与文字说明)使其极具学术价值。他还把外科治疗划分成几个部分,例如烧灼术、手术切除、放血疗法与接骨术。12世纪《医学手册》的外科部分(第30篇)在托莱多被来自意大利克雷默那的翻译家杰拉德(1114~1187年)翻译成拉丁语,并且在1497~1544年之间至少再版10次之多。12~15世纪几乎欧洲所有的医学家编撰的外科教科书无不参考或引用扎哈拉维原书的译本,例如Roger、Guglielmo Salicefte、Lanfranchi、Henri de Mondeville、Mondinus、Bruno、Guy de Chaulliac、Valescus、Nicholas及Leonardo da Bertapagatie等人。在《医学手册》的第一与第二篇里扎哈拉维归类325种疾病,讨论它们的症状与治疗,并且在第145页上首次描述一种由“健康”母亲传递给儿子的出血性疾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血友病。这部分篇幅后来亦有拉丁文译本出现,名为“Liber Thoricae”。

(六)在妇产科方面扎哈拉维的著作包括指导训练助产士如何处理异常分娩,取出死胎与去除胎盘以及剖腹产的实施方法等。出生在西班牙的医学家伊本·拉希德(1126~1198年)是研究组织学的先驱,他还发现患过天花的人以后不会沾染天花,他对血管与运动保健也颇有研究,西班牙与北非的摩洛哥都曾留下他工作的足迹。他的《医学原理》在当时是一部很全面的医学入门书籍,除了医学之外哲学与天文学也是伊本·拉希德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在哲学方面他的“阿威罗伊哲学”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甚至大大胜过其在伊斯兰世界所享有的威望。阿拉伯帝国的医学非常注重眼科疾病,医生们好像大多都对这方面的病症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具有很高的诊断与治疗眼科疾病的技艺。几乎所有的医学著作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眼科疾病,但是最全面的关于眼科疾病的论述是以专著的形式讲述的。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年,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基督徒)写了多部眼科学专著,诸如《眼科问题》、《眼睛的结构》、《五彩斑斓》、《眼科疾病》、《眼病治疗》、《眼科疾病的手术疗法》等,其中以《眼科十论》影响最大,卡哈尔(940~ 1010年,基督徒)则在其眼科学专著《眼科医师手册》里介绍多达130种眼科疾病。
(七)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其病变部位在眼球的晶状体,未治者的结局常常是致盲。当时聪明的医生已经知道它的治疗方法,与卡哈尔同时代的毛斯里是白内障针吸术的发明者,这种技术即通过一种金属空心针经过巩膜吸除白内障病变。200多年后的1230年有一位历史学家兼眼科医生在大马士革的一家医院里亲眼目睹过使用上述器械去除白内障的手术的过程,然而14世纪埃及著名的眼科医生萨达卡对这种疗法的真实性表示质疑。沙眼是又一眼科常见疾病,常引起倒睫、睑内翻及角膜血管翳,严重者也可致盲。当时的医生对于此症已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不但对角膜血管翳给予清晰的描述,而且尤其擅长于手术切除这种长在角膜上的血管组织,但是这种手术的真实性似乎令人疑惑。他们在手术中使用一系列自己发明的手术器械,例如开眼器、拉钩、细小的手术刀和拨针。他们还能够采用类似的手术器械治疗翼状胬肉,以当时的医学水平来看上述手术是非常精细与复杂的,而且患者往往要忍受相当程度的疼痛,故帝国的医生可能并非常规进行这种手术。12~14世纪在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出现许多眼科学著作,例如《眼科指南》与《眼科疾病治疗的思考》等,后者分17章讲述眼的解剖、生理以及124种眼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其中不乏在作者之前从未描述过的内容,它们在当时以及其后几百年间都是从医者学习眼科疾病的权威著作。

(八)虽然眼科疾病早先一般是在外科疾病中讨论的,但是阿拉伯帝国的医生已经开始把眼科疾病从一般医学中独立出来,这就是现代眼科学学科的雏形。13世纪叙利亚医学家库弗(1233~1286年)在其编写的外科专用手册里故意不收入任何眼科疾病,因为在他看来眼部疾病应该属于专科医生的诊治范畴。哈森(965~1040年)不仅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在研究光学原理的同时也对人类眼科学或眼科生理学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他的研究丰富人们对于眼球的生理解剖和视觉原理的认识,今天眼科医生使用的视网膜、角膜、玻璃体及前房液等专业术语据说大多是哈森发明的。穆斯林是研究精神疾病的开拓者,而且在这一领域发挥早期的作用,事实上这归功于拉齐的直接贡献,是他在巴格达为精神疾病患者建立特别的病房。正如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教授赛义德所言:“穆斯林为精神病学带来一种冷静的全新的意识,因为穆斯林医学家根本不会相信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盛行的精神疾病的‘鬼魂学说’(鬼魂附体),所以他们能够对此类疾病进行冷静的临床观察。”13世纪大马士革的医学家纳菲(1213~1288年)对盖仑的血液循环学说进行积极的批判,盖仑认为血液的流程是右心腔→左心腔,而纳菲发现心脏左右心腔之间的隔膜很厚,而且隔膜上面没有像盖伦所设想的那种孔道,血液不可能从右心腔直接流至左心腔。
(九)为了纠正盖仑的谬误,纳菲斯提出一种血液小循环(肺循环)理论,即血液在此的流程是右心腔→肺动脉→肺(交换空气)→肺静脉→左心腔,这种血液小循环理论比后来的塞尔维特(1511~1553年,因蔑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被宗教裁判所裁决处死)的发现要早300多年。遗憾的是他的学说并未在当时引起人们的重视,被淹没700多年直至20世纪才重新被后人在布满尘埃的档案中发现。1547年安德里亚·阿尔帕戈曾经将伊本·纳菲斯的一些书稿翻译成拉丁语,因此欧洲人完全有条件了解伊本·纳菲的重要工作(甚至包括直接阅读阿拉伯语书稿),而就在这前后欧洲的医学家便获得与伊本·纳菲斯相同的“发现”。伊本·纳菲斯不仅正确揭示肺的解剖结构,而且还是第一位记录心脏冠状动脉血液循环的医学家。他写到:“心脏的营养物质来自沿这些血管运行的血液,而这些血管是分布于心脏的。”在药物学方面阿拉伯帝国的医生与药物学家做出有益的尝试与大量的创新,他们善于使用复方制剂,主药、佐药与替代药巧妙搭配,首先开始将樟脑、氯化氨与番泻叶等作为药物加以使用。在他们的处方里还出现来自中国、东南亚、喜马拉雅山脉以及非洲的药物,而糖浆、软膏、搽剂、油剂、乳剂或脂等剂型以及丸药的金、银箔外衣则是他们首创的,甚至今天西方医学界使用的糖浆、苏打水等词汇都是从阿拉伯语音译的。

(十)当时的医学百科全书或综合性医学书籍都留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药物以及处方药物的搭配,这部分章节系统地讲解药物与处方的构成成分与配制的程序和步骤。伊本·贝塔尔(1188~1248年)是中世纪最伟大的药用植物学家,他编写两部医药学著作《药物学集成》与《医方汇编》,堪称经典之作。其中药物是根据它们的治疗作用进行编排的,而且除了阿拉伯语名称之外还加上希腊语和拉丁语名称,从而促进医药学知识在欧洲的传播。《医方汇编》的拉丁语译本的若干部分,1758年还曾在意大利的克雷默那出版。穆斯林的药物学成就对欧洲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后来相当长时期内欧洲这方面的著作,主要就是在先前穆斯林著作的基础上编辑或是稍做改编而成的。例如约翰尼斯1250年完成的《Expositio Supra Nicolai Antidotarium》(分别于1495、1599和1602年在威尼斯出版),阿尔巴诺(1306~1316在帕多瓦任教)的《Conciliator and De Venenorum Remediis》则是广泛承袭伊本·拉希德等人的著述。15世纪萨拉迪尼·阿斯科罗的《Compendium Aromatariorum》(药剂师手册),在形式和内容上深受穆斯林医学家伊本·西那等人的影响。而17世纪晚期出版的《伦敦药典》在编列的药物分类和剂型种类上也反映出受到穆斯林药物学影响的程度,事实上欧洲人使用的药典一直依赖穆斯林的著作与资料,直至19世纪晚期。
(十一)关于从医者的职业操守,伊斯兰哲学家、宗教学者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提出一个做医师的人必须在道德上具有良好的品质,即仁慈、富有同情心、友善、忍辱、接受负面批评。他对医师外表的要求是,医师应该留短发,勤剪指甲,穿戴干净,举止尊严。在众多科学学科中医药学是穆斯林的长处所在,这种地位的取得与学科教育是分不开的。而早在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初期的765年巴格达就建立医科学校培养医药学人才,阿拉伯帝国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661~750年)就在大马士革建立医院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但是有文献可考的世界上第一所正规医院是9世纪在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建立的。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又有五所医院在巴格达开业,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初期医院则是东征的十字军在伊斯兰世界开阔眼界之后,返回欧洲13世纪在巴黎建立的,与巴格达的医院相差约有400年的时间,931年帝国还规定城市或医院的医生必须通过考试才可以开业行医(据说先前的罗马帝国也有城市医生需要通过考试的规定),根据记述10世纪初期那里已经建立起流动医院,日常在帝国的村庄提供医疗服务。

(十二)巴格达最具规模的一所医院建立于982年,该院建院之初就拥有包括眼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含正骨医师)在内的25名医生,而到1184年一位旅行家描述说那所医院的规模就像是一个巨型的宫殿,另外努里医院是12世纪在大马士革建立的。872年帝国在开罗建立的一所医院,它是迄今最早的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医疗的医院。12世纪与13世纪纳斯里医院和曼苏里医院先后在开罗建立,相对巴格达而言在穆斯林管理下的西班牙中医院出现的比较晚一些。帝国的医院在设计上即为其赋予非常完善的功能。目前了解比较多的是关于12~13世纪叙利亚与埃及的医院的情况。那里的医院在布局上呈纵横交叉垂直形状,中央部分是四个拱形大厅,比邻有药房、储藏间、图书室、工作人员生活区以及厨房,每个拱形大厅都有喷水池提供干净的水源。不同的疾病诸如胃肠道疾病尤其是痢疾与腹泻、风湿性疾病、外科疾病、眼科疾病和发热等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就诊,而女性患者则是在独立的诊室与病房就诊的。医院还为精神病开辟专门的病房,医院不仅配置正常的执业医生与药剂师,而且安排有值班医生接诊预约定时复诊的病人。当时的医院同时具有医学教学功能,并且有管理、护理与勤务人员从事工作,还有医学生为非专业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
(十三)所有医院的建立与运营在财政上主要依靠的是国家预算,这笔预算来源于国家(向富人)征收的遗产税。另外富人与统治者的捐赠也为医院提供资金(伊斯兰教教义要求生活宽余者应该用部分节余帮助穷人,给予的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金钱,即交纳“天课”),虽然独立的行医者是收取一定的费用的,但是医院的服务据说是免费的,阿拉伯早期医学在病理上继承古希腊医学理论。阿拉伯医学允许在治疗方面依靠医生(含非穆斯林的医生),在伊斯兰国家中众多的基督教徒(包括基督教教职人员)以医为业或从事医学研究,他们得到政府和老百姓的尊重。9世纪中叶巴格达哈里发政府曾对860个未获得医务执照的医生进行考试,通过考试者才能开业行医,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一批从事眼科、外科、妇科等专业医生迅速成长,还出现一些女医生。医院建设方面在707年倭马亚王朝瓦利德一世建立收容盲人和麻疯病人的处所,还建立一座医院。9世纪初巴格达建立第一所医院,以后各地先后建立34所医院(还有一些流动医院)。到1109年仅巴格达的医院就达60座,此外大马士革、开罗、亚历山大、科尔多瓦等各大城市的医院都非常著名。医院建筑恢弘,内分妇女病室、专科病室、传染病室等,实行免费治疗。

(十四)在药物逐渐增多后药学自医学中分离出来,药师成为一种专业,法规与政令中明确规定药师的地位,而这种规定很快就经西班牙传遍欧洲与阿拉伯其他领地。8~10世纪以巴格达为中心的“翻译运动”中大量古希腊、印度、迦勒底(巴比伦)、埃及和波斯的医学典籍被翻译为阿拉伯文,为医学研究创造良好条件,出现一批有影响的医学家,尤以拉齐、伊本·西那、宰赫拉威和伊本·左胡尔最为著名。阿拉伯医学对世界医学的影响很大,重要的阿拉伯医学典籍都译成西方文字。因《医典》等阿拉伯医学著作在欧洲流传较较久,一些英语药名还保留阿拉伯语音译,许多医学术语出自阿拉伯语。阿拉伯与中国很早就有药物交流,晋人张华《博物志》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据统计汉代张骞及其随员出使西域,带回的植物种子除胡桃外还有葡萄、安石榴、胡瓜、胡豆、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药用植物。唐朝时期6世纪初起波斯及中亚诸国献的或与中国交易的药物有琥珀、真珠、朱沙、水银、熏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香附、雌黄等多种,唐代杜环所撰的《经行记》为较早记述伊斯兰国家药物及医术的书籍。段成式(803~863年0撰写的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记录数十种阿拉伯动物、植物药的名称,对其性状描述得很具体。晚唐、五代时经营香药的波斯人后裔文学家、药物学家李珣所撰《海药本草》收药124种(以阿拉伯药物居多),对《神农本草》、《名医别录》、《唐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起到补充作用。
(十五)北宋初年中国与大食商人的海上贸易再度兴起,当时一次输入的阿拉伯乳香就达数十万斤。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借鉴古希腊医药学的传统,善用有机矿物药。宋代有一种阿拉伯语称“摩西(穆萨)的石头”(黑琥珀,即煤精石)的药物传入中国,该药内含焦油等成分,可解蛇毒及其他动、植物之毒。997年大食商船队的首领将一块珍贵的药材“无名异”(能治疗脓肿、瘫痪、癫痫、肺大出血、尿道炎、膀胱炎等多种疾病)献给宋太宗,制药技术方面伊本·西那创用的以金、银箔丸衣保质、防腐的技术,在宋代广泛运用。元初阿拉伯、中亚及波斯等地的医生及药物大量进入中国,阿拉伯医学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定宗(1246~1248年)时有希腊血统的阿拉伯天文学家、医学家爱薛(1227~1308年)为元朝服务,爱薛于1270年成立京师医药院(其提举为正三品,级别仅次于太医院),由其妻撒刺主持。1273年春正月京师医药院改广惠司,仍由爱薛掌管。不久爱薛擢秘书监,领崇福使,迁翰林学士,兼修国史。秘书监搜藏的23种回回书籍,有些是爱薛和扎马鲁丁从国外搜集的,有些是爱薛编订的。后任平章政事,1307年封秦国公。次年去世,追封拂菻王,谥忠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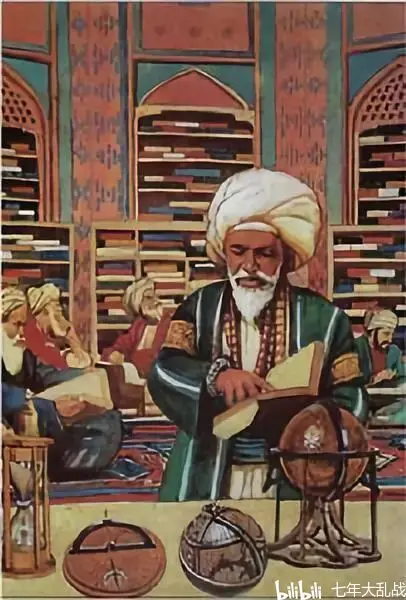
(十六)据《元史》载元代朝廷专设六个机构研究和推广阿拉伯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从阿拉伯来的医生,能治疗多种疑难杂症,还能进行外科手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元大都北京回回医生曾为一小儿做过开额切除肿瘤手术,活跃于民间的回回医生因其医术高超而受到人们赞誉。元人王沂《老胡卖药歌》曰:“西域胡贾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师心已解工名术,疗病何须说《难经》。”1382年翰林李翀、吴伯宗受皇帝召与钦天监灵台郎海达儿、阿答兀丁、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合作翻译阿拉伯文天文书等,《回回药方》于同期译出,这是明代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回回药方》的内容多来自元代阿拉伯医书,是阿拉伯医药方剂的汇编,原文为阿拉伯文。明初经翻译木刻印刷成书,著、译者均未署名(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收藏)。现存的《回回药方》为残本四卷,计485页,约20万字。共载方剂450余个,兼以病理治疗分析(有研究者推断《回回药方》全书的方剂约有7000余个)。《回回药方》极大地丰富中医的本草学,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瑰宝。

(十七)阿拉伯医学对传统中医学的医药经典著作也有重要影响,明初朱橚、滕硕、刘醇同编的《普济方》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均录有阿拉伯医方。有的药名是用阿拉伯药名,如朵梯牙(天然硫酸锌)、安咱芦(波斯树胶)、可铁刺(西黄耆胶)、阿飞勇(鸦片)、红石扁豆(鸡血石)、李子树胶(阿拉伯树胶)、咱甫兰(藏红花、番栀子花)、鸡子清、火煅大海螺、炼酥铜、奶女儿汁(奶汁、乳汁)、白雪粉(铅白)等。自清代起阿拉伯医学与中医进一步融合,一些药方和疗法已经成为中医药物学的内容。医学理论上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根据阿拉伯医学解剖知识在《天方性理》中提出人的眼、耳、口、鼻以及四肢百体均各有所司,但大脑为百脉之总源,而百体之知觉运动皆赖焉。在中国心理医学史上较早明确揭示人的器官活动与感知心理的生理基础,一些阿拉伯医生的后裔运用新技术发展医药业。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医学有较大影响,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邀请大食、印度和内地的医生各1名到吐蕃编撰医书,大食医生写了《主要文集补编》。三位医生合编综合性医书《无畏的武器》,全书共七卷,包括三种不同来源的医学。《维吾尔医常用复方制剂手册》里也保留有《医典》的内容,《维吾尔药志》(上册)110余种本草的名字有半数以上沿用阿拉伯语称谓。
怛罗斯之战
(一)六到八世纪欧亚大陆上有三个大帝国正处于兴盛期,分别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西域诸国、西突厥汗国先后被唐朝所灭,唐朝扩张并且开始统治河套、漠南、西域、漠北、安南等地。伊吾(哈密)、鄯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域小国或被迫投降于唐朝,或被武力灭国,唐朝从此建立以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几乎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从阿拉伯半岛开始经过战争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大帝国,向西占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吞并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控制地中海南岸的整个地区,阿拉伯帝国成为唐朝之外影响中亚的另一力量。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唐朝的领土就任命谁做唐朝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印度的边疆地区,屠杀、赶走大量非穆斯林,后者征服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谁都没能跨过唐朝的国界。715年阿拉伯联合吐蕃进攻中亚锡尔河的国家拔汗那,被唐军击败。阿拉伯帝国由于地理上的巨大优势,影响力慢慢的体现出来,中亚诸国原本大多信奉佛教、祆教等或自己的传统宗教,对伊斯兰文化的东进感到不安,于是不少国家向唐朝求援。

(二)而突骑施由亲唐转变为反唐,736年盖嘉运指挥唐军大破突骑施,739年盖嘉运指挥唐军大胜突骑施,突骑施可汗苏禄被杀,突骑施新可汗吐火仙、黑姓可汗尔微都被唐军擒获。741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勃律(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娶吐蕃公主,小勃律国地处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要道。747年高仙芝率唐军步骑一万进行长途远征,从安西出发,用百余日到达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连云堡地势险要,且有万人吐蕃兵防守,但高仙芝指挥下的唐军作战神勇,半天时间便攻占该城。吐蕃在娑勒城聚集十万军队,高仙芝在夜里指挥军队渡河,派李嗣业率领唐军发起进攻,打的吐蕃军惨败。吐蕃军大溃败,逃跑时十分之八、九的人摔死、溺死。此后高仙芝率兵继续深入,越过险峻的坦驹岭进入阿弩越城攻占小勃律国,派唐军驻守小勃律国,高仙芝带着活捉的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返回。此役之后唐军在西域威名更盛,高仙芝也被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749年阿拉伯政权从倭马亚家族转入阿拔斯家族掌握,即使在西亚亦成定局。而在怛罗斯之战一年以前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已经迅速迅速彻底打垮阿拉伯倭马亚王朝,能够调大量军队到东部来。呼罗珊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地,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能从这里派出庞大的军队。据塔巴里的记述阿拉伯叶海亚在呼罗珊的一次征兵,应征入伍的士卒达50万人之多。
(三)而从怛罗斯之战到叶海亚在呼罗珊这次征兵之间这段时期呼罗珊并没有发生能导致兵源发生大变化的事,可见怛罗斯之战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能从呼罗珊出动大量军队。此外关于怛罗斯之战,查阅大量阿拉伯史料的权威历史学家王小甫指出呼罗珊屯聚着阿拉伯阿拔斯军队的主力,可见阿拉伯能动用大量主力军队参与怛罗斯之战。750年高仙芝再度奉命出军,击破亲附吐蕃的车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这两次艰难的远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获得极大的声誉。此时唐朝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他控制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俨然是大唐在中亚的总督。750年高仙芝还击破石国及突骑施,高仙芝以石国“无番臣礼”为由征讨石国,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掳走石国国王及其部众,格杀老人与小孩,搜取财物。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高仙芝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并将石国国王斩首。此时高仙芝达到征战生涯的最高峰,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求救,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怛罗斯城是石国的第二大据点,《新唐书·石国传》记载:“怛罗斯城,石国常分兵以镇之。”这也是高仙芝与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

(四)距离怛罗斯城不远的撒马尔罕早已是大食兵聚集的据点,高仙芝并不知大食的意图,而且唐在葱岭以西的属国分散部署,一时很难集结。为了阻止大食的东进,以攻为守,远征大食对于深谙兵法的高仙芝来说似乎成为可行手段。刚刚平定布哈拉和粟特的叛乱的阿拉伯大军南下恰好与高仙芝大军相遇在怛罗斯河,高仙芝于751年四月从安西出发,在翻过帕米尔高原(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高仙芝在七月份到达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逻斯,并且开始围攻怛逻斯城。由于阿拉伯人早就在准备对安西四镇的攻击,在接到高仙芝进攻的消息之后立即组织十余万的大军赶往怛罗斯城,双方在怛逻斯河两岸附近展开决战。高仙芝军队与阿拉伯军交战5天,打成平手。阿拉伯重金收买葛逻禄,葛逻禄突然反叛,与阿拉伯军夹击唐军,导致唐军战败。高仙芝的军队与阿拉伯军相持五天,葛逻禄部众突然反叛,与阿拉伯军夹击唐军,导致高仙芝失败,只剩下数千人返回。高仙芝军队由数千唐军与2万多葛逻禄军、拔汉那军组成,《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记载高仙芝军队数量为3万人,最后有数千唐军返回安西。以此计算时唐军至多损失数千人,主要减员数量是投敌的葛逻禄军与损失的拔汉那军。《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九、《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三都记载高仙芝军队数量为2万人,最后有数千唐军返回,以此计算时唐军至多损失数千人,主要减员数量是投敌的葛逻禄军与损失的拔汉那军。
(五)怛罗斯之战后第二年安西唐军在驻守安西各地的情况下还能分兵远征大胜吐蕃,攻占吐蕃战略要地大勃律,阿拉伯立即派人求和于唐朝。也说明怛罗斯之战唐军的损失很小,安西唐军的实力没有被怛罗斯之战削弱。在怛罗斯战役后唐朝仍然控制西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立即派人来与唐朝讲和。唐朝与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并未见受到此战的显著影响,阿拔斯在对唐关系方面上与前朝没有什么改变,自战后的6年每年均有阿拔斯使臣来朝,仅753年就来了四次,在怛罗斯之战之后中亚的拔汗那、倶密、康国、安国及花拉子模等等国家仍然遣使朝贡于唐朝。怛罗斯之战之后高仙芝仍被玄宗委以重用,755年安禄山叛反于范阳,高仙芝奉命征讨叛军并扼守潼关,遗憾的是不久玄宗听信谗言错斩高仙芝。怛罗斯之役后不久阿布·穆斯林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而唐朝方面由于几年后爆发安史之乱,之后还有朱泚之乱、藩镇之祸等数次内斗导致国力消耗,没有再进军河中地区,并不存在吐蕃与阿拉伯3次大战、十几万精锐损失殆尽、吐蕃挡住阿拉伯东进防止西域中国被伊斯兰化等事。事实上所谓的那几个吐蕃与阿拉伯大战的时期阿拉伯主要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无力顾及伊斯兰化西域、唐朝,当时阿拉伯在东部倒是与古斯、突厥有过冲突。

(六)作为当事人的阿拉伯的史料记载里,那时没有吐蕃与阿拉伯大规模交战、十几万精锐损失殆尽,倒是有阿拉伯人造惹瑟知之门等防御突厥人的侵袭,在布哈拉、赭时等地区修筑城墙以防御突厥人的侵袭。支持拉斐厄叛乱的战士来自10多个势力,其中突厥人起重要作用,拉斐厄见弃于突厥人之后很快就投降于阿拉伯马蒙。法德勒东征打多个势力,虽然有俘获吐蕃军官,但是其与吐蕃的交战规模极小、影响很小,记载很简略,还比不上对怛罗斯之战的记载。法德勒东征其实不是吐蕃与阿拉伯大战,而且法德勒东征本来也没有伊斯兰化西域、中国的能力。阿拉伯史料里根据塔巴里、亚尔库比、加尔迪齐等人的记载,阿拉伯与吐蕃大战的那个时间段波斯人的暴动、什叶派运动不断,阿拔斯大食委派的历任呼罗珊省总督不得不应付波斯人乃至阿拉伯人本身发动的一系列叛乱。谢里克事件平息后布哈拉什叶派阿拉伯人仍不断背叛,哈里吉派优素福.贝尔木之乱、曼苏尔.本.阿卜杜拉之乱、塞吉斯坦与巴德吉斯屡次动乱、阿什纳斯之乱等等。当时阿拉伯主要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阿拉伯史料记载马赫迪分遣使节要求若干国家的统治者称藩纳贡,其中多数应命臣服。
(七)史籍载称应命称藩者有粟特的伊赫施德、乌什鲁桑那的阿弗申、费尔干纳的君主、葛逻禄的叶护、九姓乌古斯的可汗、突厥人之王答儿汗、吐蕃王。 当哈仑.拉施德在位时(786-809年)总督吉特里夫.本.阿塔(792-3年)为了驱逐葛逻禄叶护的军队派遣阿慕尔.本.杰米勒进入费尔干纳,阿拉伯史料记载806-810年拉斐厄叛乱,拉斐厄的战士中有来自赭时、突厥、费尔干纳、忽毡、乌什鲁桑那、石汗那、布哈拉、花剌子模、珂咄罗、古斯、葛逻禄等10多个势力,主要是突厥、古斯与大食冲突,而非吐蕃。拉斐厄于809年见弃于突厥人, 当他听到马蒙为政清明的报告时遂也向马蒙纳降,得到后者的宽宥,既往不咎。810年这次变乱完全平息,拉斐厄见弃于突厥人不久,这次变乱就完全平息,可见突厥对这次变乱影响之大。大食的马蒙在对哈利发阿敏(811年)展开斗争以前曾向其韦齐尔法兹勒.本.萨赫勒诉说:“葛逻禄、叶护、吐蕃主可汗不臣服,喀布尔王正要夺取呼罗珊与喀布尔毗连的地区,讹答剌君主不肯继续入贡。”马蒙听从法兹勒的建议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大战,之后也没有大食与吐蕃大规模交战的记载,而是大食对付突厥、古斯以及反叛的大食人、波斯人。伊本.忽尔达兹比在其《道里与诸国志》说:“惹瑟知是呼罗珊在那个方向最遥远的地点,它位于两山之间。突厥人常常经由此处前来侵袭,所以Barmak家族的法德勒在那儿建造一座大门。”

(八)根据奈尔沙希、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等人记载,阿拉伯人在布哈拉、赭时等地区修筑城墙以防御突厥人的侵袭。当时大食集中力量解决反叛、内讧以及与拜占庭的冲突,而在大食的东部中大食与古斯、突厥有冲突,大食在布哈拉、赭时等地区修筑城墙以防御突厥人的侵袭,没有要准备攻打伊斯兰化西域、唐朝。实际上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唐军就连续派兵在西域活动,西域各国也多向唐朝朝贡,虽然有些小国投靠阿拉伯,但亦有背叛阿拉伯重新倒向唐朝的。怛罗斯之战的爆发本与石国有关,但是战后不久石国仍然倒向唐朝。从新近出土资料中也有很多怛罗斯之战后唐朝中央与中亚地区军事据点的文书往来,纵观唐朝的扩张史偶遭挫折并不少见,而败后卷土重来也是唐朝惯用的战略。假如安史之乱不爆发,大唐仍维持表面上的繁荣,那么若干年后唐军再次出击中亚,与阿拉伯军队再次相遇几乎是必然的,当然这仅仅是假设。安史之乱的爆发引爆唐朝社会的几乎所有矛盾,即使怛罗斯之战取胜,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时唐朝势力仍会撤出中亚。法国学者张日铭在著作中认为在安禄山叛乱前唐从未自西域撤退,所以正好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当口爆发怛罗斯之战,而不是怛罗斯之战促使唐朝由盛转衰。造纸术被误传为经过怛罗斯之战西传,实际根据杜环《经行记》的记载被俘的工匠里没有造纸工匠。
(九)有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怛罗斯之战之前造纸术就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拔汉那首府浩罕传往撒马尔罕,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导致唐朝无力染指葱岭以西的中亚,并自此退出对中亚霸权的争夺,原本臣服于唐朝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尽管阿拔斯王朝取得怛罗斯战役的胜利,但是慑于对唐军在怛罗斯战役中展现的惊人战斗力,阿拔斯王朝也打消东进扩展领土的打算,只是默许葛罗禄在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附近的扩张。他们自立一国家,并一直维持至九世纪末被后来建立Kara-Khanid Khanate的入侵者消灭。杜环是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宝贵的记录。怛罗斯战役后中亚大部分地区并没迅速地转化为伊斯兰教区,虽然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建制很早,但阿拉伯人对当地人仍非常不信任,主要是他们并非伊斯兰教徒。初期的时候为了增加税收没有要求人们该信伊斯兰教,到了屈底波时期开始约许免税引诱和强迫人们改教,不过一直到了850年的萨曼王朝时期伊斯兰教才逐渐成为河中地区主要信奉的宗教。而在唐安西四镇、北庭所在,即使在790年以后唐朝退出西域舞台,当地也没有因此转化为伊斯兰区。回鹘及后起的几个突厥政权一直扮演汉传佛教的守护者,一度代表汉传佛教势力抵抗伊斯兰教。

(十)到了950年前后喀喇汗国统治者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在新疆得到发展,在新j东部地区的高昌回鹘仍信奉佛教,新j境内一直到15世纪末明代中叶才完成全盘伊斯兰化,此时距怛罗斯战役已有700年,而唐朝也于907年灭亡。回鹘本信奉摩尼教,摩尼教于763年传入蒙古回鹘汗国,迅速发展成为国教,其影响渗透到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直至840年回鹘汗国崩溃,部众西迁至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受到当地盛行的汉传佛教的影响,大批民众多改信佛教。唐代的新疆地区是汉传佛教的一大中心,已有了近很长的汉传佛教发展历史,僧徒众多,香火旺盛。这些都为后来回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佛经、回鹘佛教石窟艺术诸因素来看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影响最大。虽然吐蕃曾在新j统治一段时间,但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影响仍不及汉传佛教。直到元代由于蒙古人崇敬喇嘛,藏传佛教才在新j得到发展。但汉文佛典被翻译为回鹘文的数量仍最多,大约81部41种佛经,其次才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佛经,至少有16部。匈牙利学者Harmatta推断在蔡伦发明纸张后的一个世纪索格低亚就已经用纸通信,到了3世纪纸张已传入伊拉克地区。李约瑟指出早在650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到了707年纸张已在阿拉伯半岛麦加被阿拉伯人使用,总之都比怛罗斯战役早。
葛逻禄
(一)拔汗那是中亚古国,在锡尔河中游谷地,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地区。汉代称大宛,中国古籍又作破洛那、钹汗沛汗、拔汗那、跋贺那等,都西鞬城,此国已由酋豪割据数十年。627~649年间其王契苾为西突厥瞰土屯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其子遏波之立契苾的侄子阿了参为王,统治呼闷城(今列宁纳巴德),遏波之统治渴塞城(今长散)。唐破西突厥在658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府,授阿了参刺史。武周时期郭虔瓘和阿史那忠节擅自攻入拔汗那,征收盔甲与战马,当时郭元振在疏勒国访问,但不曾听闻得到一甲一马。拔汗那忍受不了武周的侵扰便于693年向南勾结吐蕃,又搀扶西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进犯武周的安西四镇,最终被武周击败。713年、715年大食异密屈底波侵入拔汗那,与吐蕃共立阿了达为王,原拔汗那王奔安西求救。屈底波死后张孝嵩率兵万余人长驱数千里,攻阿了达于连城,阿了达携数骑逃入山谷。720年阿了达复为拔汗那王,722年答应反阿拉伯的粟特人前来避难,又把他们出卖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进入拔汗那,阿了达伪降而夜袭之,兵败被杀。旅居中国的新罗僧人慧超(726~727)经过时此地有两王,锡尔河南一王属大食,河b一王属突厥。738年突骑施可汗苏禄败亡后阿拉伯派一总督前往拔汗那,但仍无法控制。739年阿悉烂达汗助唐平突骑施可汗吐火仙,被册封奉化王。
(二)744年唐改其国号宁远,嫁和义公主于此。754年王忠节遣子薛裕入唐,755年授薛裕左武卫将军,放还拔汗那。拔汗那复派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西德、麦蒙亦相继派兵到拔汗那企图制止对阿拉伯统治的反抗,直到820~821年拔汗那置于萨曼家族统治之下逐渐伊斯兰化,当地王朝才告消亡。拔汗那盛产葡萄、香枣、桃、李,亦出驼、骡、羊、马之类,产朱砂、金、铁、银、铜、铅等。语异诸国,为东伊朗语之一支。葛逻禄亦称葛罗禄、卡尔鲁克等,是6~13世纪中亚的一个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为铁勒人诸部之一。地处北庭西北,金山(今阿尔泰山)之西,与车鼻部接。有三姓,一曰谋落,或谋剌;一曰炽俟,或婆匐;一曰踏实力,故文献中常称为三姓葛逻禄。首领号叶护(伊纳勒),故又号三姓叶护。葛逻禄人最早游牧于阿尔泰山南部(即新疆北部的草原),8世纪中叶迁徙至锡尔河流域、七河流域、伊犁河河谷,与费尔干纳盆地,苏坎特、白水胡城、怛罗斯成为他们的活动中心,另有一部分分布在伽色尼、巴尔赫与吐火罗斯坦地区。突厥汗国兴起以后葛逻禄属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崛起以后属薛延陀汗国。7世纪50年代初唐朝将领高侃伐车鼻部,葛逻禄归属于唐。657年唐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后又分炽俟部之大漠州为金附州都督府。三姓处在东西突厥之间,常随东西突厥之兴衰而叛附不常。

(三)742年与回鹘人、拔悉密人一起攻杀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立拔悉密酋长阿史那施为颉跌伊施可汗,葛逻禄人、回纥人之长自为左右叶护。744年葛逻禄部与回鹘部一起攻杀拔悉密部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部首领骨力裴罗(逸标苾)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746年被唐封为怀仁可汗,于是在乌德鞬山的葛逻禄部归于回纥。在阿尔泰山及北庭一带的葛逻禄自立叶护,归属于唐。751年7月-8月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安西都护府二万汉军,外加盟军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一万人与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调集的三万阿拉伯骑兵会战于怛罗斯。葛逻禄人勾结阿拉伯人,阵后偷袭唐军,致使唐军战败。755年唐朝发生内乱安史之乱,西域唐军部分被调入内地平叛,剩余唐军仍然坚守西域数十年,790年以后唐朝才失去西域。766年葛逻禄强盛起来,逐渐取代突骑施,占有楚河流域西突厥故地,其中包括著名的碎叶城、怛逻斯城。789年葛逻禄在北庭一带与吐蕃人联军,战胜回纥人,但是没有多久回鹘人进军西域,在北庭、龟兹、拔汗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败葛逻禄与吐蕃人的联军。当时漠北、西域的形势大致是漠北、天山以北是回鹘汗国;回鹘人的西北是黠戛斯人;黠戛斯人西南是葛逻禄人;葛逻禄人南是吐蕃人;葛逻禄人西南是入居中亚的阿拉伯人。他们之间有战争也有经济和文化交往。

(四)840年漠北的回鹘汗国灭亡,接近三分之一的部众(十五部)西迁,其中西迁三支之一奔葛逻禄人,和葛逻禄人融合。10世纪葛逻禄人和西迁部分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强大,葛逻禄人为喀喇汗王朝的强盛立下汗马功劳,此后七河流域的葛逻禄人活动区域成为喀喇汗王朝的半自治地区,享有一部分自治权。后来直到蒙古人入居中亚之后葛逻禄人称为哈喇鲁,在这一带仍很活跃。12世纪西辽征讨葛逻禄人,但为葛逻禄人所败。葛逻禄人属游牧民族,居处无定,楚河流域在葛逻禄人进入之前就已经有了农业,故葛逻禄人在从事游牧的同时也兼营农业。中亚粟特族商人及穆斯林传教者对葛逻禄的影响都很明显,葛逻禄人是近于文明的民族,殷勤好客,喜欢交际。葛逻禄人的国王往昔为叶护,该国有城市与乡村。有些葛逻禄人是猎人,有的是农夫,有的是牧畜者。他们是好战的民族,习于劫掠。葛逻禄人习惯于游牧和城居相结合的两栖生活,境内拥有十五座城市,其中米特克与Yhonksi二城明确记载是葛逻禄人所居,巴尔托里德还记载葛逻禄人尚黑。葛逻禄人是乌兹别克族的祖先之一,同时维吾尔族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为葛逻禄后裔。另有一部分跟随九姓乌古斯的西征融入到土克曼族、土耳其族之中,居住于阿富汗斯坦的葛逻禄人则成为部分普什图族吉尔查伊部落的祖先。
突骑施
(一)突骑施是唐代时期一边远部落,属于西突厥,在当时隶属于北庭都护府管辖,原为西突厥别部。西突厥有十姓部落,分为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五咄陆部,置五大啜。突骑施贺逻施啜即五大啜之一,突骑施散居伊犁河流域。658年唐朝在中亚广设羁縻都督府州,于突骑施部落设置过嗢鹿州和洁山两个都督府,7世纪50年代初期受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统属。658年唐平定阿史那贺鲁后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嗢鹿州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置絜山都督府,又置昆陵、蒙池两都护府以统之,并隶安西都护府。武则天时期以原领五弩失毕部之阿史那斛瑟罗为竭忠事主可汗、蒙池都护,斛瑟罗残暴,不为突厥所附。突骑施首领乌质勒本为斛瑟罗之莫贺达干(突厥官名)能抚士、有威信,胡人顺附,由此崛起。置二十都督,各督兵七千,以楚河流域之碎叶城为大牙,伊犁河流域之弓月城(今新疆霍城西北)为小牙。辖境东邻后突厥,西接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尽有斛瑟罗故地,而服属于唐。699年乌质勒遣子入朝,706年受封为怀德郡王,708年封西河郡王。使者未至而乌质勒死,子嗢鹿州都督娑葛代统其众,胜兵至三十万,唐封之为金河郡王。其将阙啜忠节与之不和,唐相宗楚客受忠节赂,支持忠节。娑葛遂袭擒忠节,杀唐使冯嘉宾,败唐安西副都护牛师奖。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以娑葛理直,表请赦除其罪,娑葛乃降,后娑葛为后突厥默啜可汗擒杀。突骑施部落领袖中比较著名的有两位,一个是苏禄可汗,一个是吐火仙可汗。

(二)突骑施可汗苏禄(717-738年)复有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苏禄收拾余众,自立为可汗,众至二十万,称雄于西域。给予当时向中亚发展的大食人以沉重打击,大食人因而称之为“抵顶者”(意为牛或象等冲撞抵顶的庞大动物)。713年唐任命苏禄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赐号忠顺可汗。时苏禄处于唐与后突厥、吐蕃之间,与三方均保持密切关系。唐以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妻之,苏禄又娶于后突厥、吐蕃,三女并为可敦。后与唐安西都护杜暹有隙,结吐蕃兵掠安西四镇,围安西城。闻杜暹入为唐相,乃退去,复遣使入朝。苏禄趁穆斯林军团的攻击所造成的混乱入侵塔里木,自692-694年起塔里木已处于唐的保护之下。苏禄包围阿克苏城(717年),数月之内骚扰唐的四镇——焉耆、库车、喀什和于阗。虽然他未能攻陷四镇,但他仍占领长期以来唐在西域的前哨基地——伊塞克湖以西的托克玛克城(碎叶城),尽管唐将阿史那献在该地打了一仗(719年)。唐朝对保住这些冒险性的要塞丧失了信心,企图以封号和爵位羁縻苏禄(722年)。724年苏禄在渴水日战争中大败倭马亚王朝的入侵军,726年劫掠成性的苏禄蹂躏四镇。731年苏禄可汗在塔什塔卡拉查之战中围攻倭马亚王朝军队,虽然未能竟全功,但倭马亚人损失惨重。渴水日战争是724年阿拉伯倭马亚王朝与突骑施汗国苏禄在锡尔河畔苦盏发生的战争,突骑施苏禄可汗接到河中粟特王国请求后出兵,并击败阿拉伯人。
(三)自712年屈底波(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征服河中后,且于714年在铁门关成功阻击东突厥阙特勤率领的20万骑兵后,河中成了华夏文明与伊斯兰势力争夺的焦点。屈底波死后第二年的715年定远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献率领五万大军从碎叶出发南下收复葱岭西各国,一举攻克阿拉伯要塞——铁门关。张孝嵩率领蕃汉兵马一万在拔汗那大败吐蕃-阿拉伯-西拔汗那联军,俘斩数千,南北唐军连下中亚数百城,震慑阿拉伯帝国。716年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曼苏尔亲自率领部下作使者出使长安,唐玄宗授予其爵位并放还被俘虏的大食官员。而当唐军东撤应对东突厥默啜对北庭的侵犯时阿拉伯再次侵占河中,并且对其利用伊斯兰教法统治,引起河中各国的反抗。720年康国、俱蜜、安国等联名奏上《请讨大食表》,唐玄宗委任金方道经略大使苏禄可汗处理此事,而时任呼罗珊总督的赛义德得知此事后于第二年发动对唐朝的进攻,大军刚刚进入葱岭不久便遭到苏禄的部下屈素律的袭击并被包围切断水源,赛义德缴纳赎金后才得逃走 。哈里发叶齐德二世大怒,撤换赛义德,并任命穆斯林·本·赛义德为新总督,于724年统率数万精锐大军讨伐河中各国。穆斯林·本·赛义德轻松攻克史国,康国国王不战而降。穆斯林·本·赛义德裹挟康国国王乌勒加以及近万康国大军东进拔汗那,拔汗那国王向苏禄求援,苏禄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联合石国、曹国、拔汗那等军队包围阿拉伯军。

(四)穆斯林·本·赛义德率领下的倭马亚军在费尔干纳听到突骑施军队南下的消息后慌忙撤退,而突骑施联军在后面边追赶边袭击。当阿拉伯军队行至曹国(渴塞城、今苦盏)时便展开军阵准备与突骑施联军决战,而突骑施联军却将精锐宗教军团分割包围,阿拉伯骑兵无法抵御突骑施骑射手的进攻纷纷败逃,康国国王乌勒加被乱箭射杀。夜晚苏禄亲自突袭阿拉伯大营,穆斯林·本·赛义德在慌乱中逃走,阿拉伯联军损失惨重,只剩下少数人撤回撒马尔罕。突骑施军队趁势将阿拉伯势力赶回阿姆河以南,河中波斯复国军得到鼓舞,攻陷巴尔赫,新总督阿萨德畏惧不前。苏禄派其儿子尔微特勒带领波斯王波善活联合塔巴里斯坦的国王进军阿塞拜疆,大马士革赶尽派出全国最精锐的骑兵驰援阿塞拜疆,波斯军队战败逃回中亚,而后苏禄亲自率领河中军队进军呼罗珊总督区,但均无功而返。于是第二年哈里发希沙姆派三名猛将——阿什拉·本·阿布拉达、朱奈德·阿卜杜拉·赫尔曼、哈登·本·屈底波又派出几万大军从大马士革出发东征突骑施,意图再次统治河中,而苏禄在阿木勒河对面休整。阿拉伯军趁其不备偷偷渡河,不料当大部分穆斯林都半渡时突骑施军队突然发起进攻,阿拉伯大军被杀者数万,阿木勒河被染红。
(五)朱奈德边战边逃,最后一路上收拢8000余残兵逃回木鹿城,于是阿拉伯人十年不敢踏入河中。 至此河中一带重新归唐朝势力,苏禄被加封为十姓可汗。736年唐北庭都护盖嘉运在古城附大破苏禄,737年苏禄在行李日之战击败阿拉伯人。此后不久在738年苏禄被处木昆部的阙律啜(即莫贺达干)杀害,处木昆似乎是地处巴尔喀什湖东南、游牧于葛逻禄和突骑施两部之间的一支小突厥部落。738年苏禄为其下大首领莫贺达干所杀,突骑施复乱,苏禄子吐火仙立,与莫贺达干相攻。娑葛之后称“黄姓”,苏禄之后称“黑姓”,更相仇杀。779年后葛逻禄强盛,据有楚河流域,突骑施二姓衰微,遂为所役属。738年莫贺达干杀死苏禄可汗,都摩度拥立苏禄可汗的儿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739年莫贺达干与唐将盖嘉运联合阻止突骑施觊觎王位者、苏禄之子吐火仙的复辟。然而所有突厥小可汗们的经历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力求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重新统一西突厥。莫贺达干很快与唐决裂,742年杀唐朝派往突骑施的都督、汉化突厥人阿史那昕。然而唐朝像往常一样又获得最终的决定权,744年唐将夫蒙灵詧打败并杀死莫贺达干,由于这次胜仗让唐朝又成伊塞克湖地区和伊犁河流域的主人。

(六)748年唐将王正见在伊塞克湖西北、楚河上游地区的托克玛克城(碎叶城)建一寺庙,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入朝,呈献被俘的另一位突骑施首领。《新唐书》突骑施传记载庞特勒可汗:“至德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唐朝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最早的突骑施首领)余部附回鹘。及其(回鹘)破灭,有庞特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突骑施传》云:“大历(766至779)中,臣于葛罗禄,余众人回鹘,及其灭也(840)。有庞特勒屠焉耆地称叶护,是焉耆回鹘,又突骑施庞特勒种也(在喀什葛尔建立喀喇汗国的庞特勒部,是居住在喀什、焉耆间的突厥人,与甘州回鹘庞特勒同名不同族)。”突骑施的最大贡献除了作为唐朝的屏障之外还有其独特的货币,突骑施汗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又处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因此作为经济交流中介手段的钱币对其有着很大的重要性。突骑施汗有自己制造的铜钱,虽然突骑施汗国地处西域的西部,自古流行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的打压式圆饼无孔钱币,但突骑施铜钱却与之完全不同。因为突骑施汗国自始至终是唐朝的属国,突骑施钱完全依照唐式的标准币——开元通宝,采用浇铸方法制造圆形方孔钱。早期制作的突骑施钱甚至大小和重量也与开元通宝相同,晚期因社会混乱和经济衰退才有轻小的异版钱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突骑施汗国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最早制造钱币的地方政权。
塔什塔卡拉查之战
(一)早在7世纪后期获得阿拉伯帝国大权的伍麦叶王朝就开始不断派兵东进,虽然只是帝国各战线中的次要方向,却给原本已进入繁盛的河中等地以重大打击。阿拉伯人也成为自公元前的马其顿军队后又一个企图以步兵征服中亚的世界强权,面对处于战力鼎盛阶段的阿拉伯士兵时分散在各城市的粟特守军显得举足无措。前者不仅有重步兵力量,还有大批可以发射重型箭头的步行射手。在从前萨珊王朝手中获得大量马匹后这些沙漠部族的战场机动力也大为加强,再算上众多主动或被动投靠新主人的波斯军队构成让河中列国都忌惮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只是在伍麦叶王朝的早期阿拉伯人还未下决心拿下河中,他们经常以呼罗珊地区的木鹿城为基地,定期劫掠粟特城市,不仅在攻克的城镇内大肆劫掠,还会向沿途商队与服软的君主敲诈贡赋。所以在穆斯林入侵的前期河中等地虽然遭到很大损失,但还可以保持最后的独立属性。不同绿洲城市间的固有矛盾也让粟特人也很难迅速结成反抗同盟,715年伍麦叶军队开始在撒马尔罕等大城市里驻扎,他们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对待本地人,并向拜火教徒与佛教徒收取宗教税,以便维持自己的军费支出。这就迫使商业贵族们开始寻求外力支援,并联系控制七河流域的西突厥联盟——突骑施。后者从第二年开始频频出兵南下,河中各地的反阿拉伯暴动也此起彼伏。虽然粟特人也知道阿拉伯征服者不是波斯人,但从地缘政治的本能来看伍麦叶王朝就在扮演中世纪前期的萨珊王朝。

(二)这种来自呼罗珊方向的强权一直是河中居民所厌恶和唾弃的对象,所以只要还有阿拉伯军队驻留木鹿就免不了同粟特人发生冲突。出兵协助起义的突厥人其实与河中的粟特人同气连枝,作为典型草原联盟的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堵在贸易伙伴的必经之路上。在萨珊王朝时期他们就帮助河中商团抵御波斯帝国的进攻,并不惜直接与对方正面冲突,如今在的阿拉伯东方驻军不过是换了名字的老对手。何况在阿拉伯人总督手下不乏主动合作的波斯贵族,很多人即便保持原有信仰也会为了利益而为新主人指点迷津。至于扮演入侵者角色的伍麦叶王朝或许在主观上没有特别针对谁的意思,但已经习惯世界征服者身份的他们不会甘愿放弃任何唾手可得的肥肉。许多派驻东方的军队成员也逐渐有了地方情节,自动扮演起曾经的波斯角色。在前朝残余势力的协助下很自然的将河中视为自己必须控制的重地,然而仅仅依靠在几个城市内的驻军根本不可能控制中亚。在724年的远征费尔干纳失败(渴水日战争)后阿拉伯人已成为困守绿洲孤岛的被包围者,他们一度希望取消宗教税来笼络城市平民,却又因为没有其他可靠的财政收入而再次作罢。恶劣的局势在之后继续发酵,迫使远在大马士革的宫廷来亲自干预。730年时任哈里发的希沙姆一世下令让原信德总督拉赫曼-穆尔里去河中任职,这意味着他必须从南方的印度河流域出发,先穿过险峻的兴都库什山,再度过阿姆河才能到任。
(三)加上首府撒马尔罕的周围已完全失控,穆尔里就必须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保护。很快一支7000人的伍麦叶军队开始奉命北上,除了新总督和驻扎北印度的阿拉伯人外军中也不乏被征服民族的辅助军、担任差役的奴隶和士兵们的家眷,因此这支部队的实际战斗人员比面上的数字要来得更少。他们在渡过阿姆河后立刻遭到四处巡弋的突骑施人攻击,依靠阿拉伯人的顽强防御和菁英武士们策马反击,新任河中总督算是在任上获得首次军事胜利。此后他又获得哈里发派遣来的呼罗珊驻军增援,开始重新攻略各主要城市。依靠数量优势和挑拨矛盾,伍麦叶军队不仅帮撒马尔罕解围,还重新控制更北方的重镇布哈拉,直到改年冬季时他才带着主力军返回呼罗珊休整。同时约有3万名各族士兵被分配到不同城镇内驻屯,以防突厥人的冬季突袭。作为突骑施联盟领袖的苏禄可汗却不愿意将自己的保护区拱手相让,他在来年开春就集结数万部族骑兵,浩浩荡荡地开始南下反攻。不仅获得撒马尔罕周围的粟特人支持,还有来自费尔干纳和塔什干的盟军协助。这迫使穆尔里在无法集结更多部队的情况下匆匆由呼罗珊北上,准备将包围首府的突厥骑兵消灭。起初穆尔里的部队约有3万多人,除了阿拉伯本族部队外还有波斯辅助部队和一些已经投靠伍麦叶当局的河中贵族,但在重返河中后他发现突骑施人就已经开始坚壁清野战略。

(四)这些草原战士不仅在沿途填埋水井,还会摧毁草场和果园,让大规模行动变得困难重重。因此穆尔里决定改道,迂回走四周陡峭的塔什塔卡拉查山口,避开突骑施人的战略堵截。但在长达2公里的山谷内行军纵队很容易被伏兵所重创,所以在总督宣布自己的计划后很多长期驻扎河中的士兵与粟特附庸纷纷表示强烈反对。一些人索性开溜,更有甚者投奔到突厥那边,将阿拉伯军队的情况告知突骑施人。但穆尔里心意已决,还是继续率领剩下的2.8万人进抵山口位置。出于谨慎考虑的他让全军在进入关口前扎营,准备进一步观察局势变化。得到消息的苏禄可汗立刻解除对撒马尔罕的围困,率军赶来阻止对方入关。当发现对手依然停留在距离山谷入口尚远的位置后突厥人没有选择守株待兔,而是全军通过塔什塔卡拉查,发起草原式的骑兵突袭。由于全军正在吃饭,阿拉伯人对这次攻击有些措手不及,担任骑兵的菁英武士立刻上马迎战,为需要时间结阵的步兵争取时间。但突厥骑射手却不与他们直接碰撞,而是调头向后逃窜,引得阿拉伯人险些掉入己方重骑兵的伏击圈。随后为伍麦叶军队担任辅助部队的波斯骑兵也被击退,造成整个阿拉伯大军的前卫分队溃败。占据数量和士气优势的突厥人一路追着对手,冲到伍麦叶主力军的临时营地跟前。在那里他们看到已经组成严密方阵的阿拉伯步兵,靠着骑兵同行们的努力在此时的阿拉伯步兵已经完成战前部署,无论是来自叙利亚地区的西方部落还是来自两河流域的东方部落都由身披锁子甲的重装战士担任第一线部队。
(五)前者使用类似拜占庭军队的圆盾结阵,用2-3米的长矛组成骑兵不敢轻易硬闯的枪林。后者则用东方式的矩形盾牌列阵,手持1-2米的标枪迎击,在他们的身后则是众多负责火力掩护的弓箭手。靠近叙利亚地区的士兵会使用发射重型箭头的单体弓,接近两河区域的士兵则习惯使用波斯式的轻型复合弓。总督和他的披甲亲卫队一同骑马居于步兵战线的后方压阵,先前败退的骑兵也回到日常的两翼靠后位置。面对这样的密集队列时突厥重骑兵迅速折返,脱离对方的弓箭射程。大量的轻骑兵重返一线,迅速射出几波密集箭矢。不少人开始从两翼迂回,打击缺乏密集队形保护的伍麦叶骑兵。但阿拉伯军队的各族骑兵也大都配有弓箭,可以在原地展开反击,部分阿拉伯重骑兵甚至主动下马,以重步兵的方式作战。苏禄可汗的部队便稍稍后撤,在完成重组后继续上前挑战,以三面合围之势加以强攻。如果有需要再次折返,和突骑施结盟的粟特武士便会接替上前。他们身披远胜大部分突厥部落兵的重甲,尝试冲破伍麦叶人的盾牌阵。在这样的持续环攻下一些不熟悉此类情况的阿拉伯分队开始动摇,穆尔里立刻下马走入全军的中心位置,以此向众人表示自己会与士兵同生共死,绝不会因占据不利而临阵脱逃。在他的激励下那些不同意这条行军路线的部落领袖虽然在嘴上不停嘲讽,却也督促属下坚持到底。趁着突厥与粟特人进攻的间隙,阿拉伯军中的奴隶们会上前进行快速作业,他们迅速用铁锹和铲子挖掘出防御壕沟,并将挖出来的土也堆成胸墙。

(六)由于没有盾牌和其他护具,这些人在突厥骑兵的复合弓火力前特别脆弱,不少人就这样被杀死在全军的最前沿位置。但正是他们的努力让伍麦叶军队的正面防御更加稳固,疲惫不堪的突厥人终于在几小时的尝试后选择暂避锋芒。第二天突骑施与粟特联军再次开始围攻,战况也如前一日般紧张胶着。在发现正面强攻无果后苏禄可汗索性让重骑兵到二线位置休息,只派轻骑兵继续包围袭扰,尤其是防御最为薄弱的辎重队伍遭到中亚复合弓的大量杀伤。穆尔里也意识到如果不打破这种僵局,全军都会在补给消耗完毕后出现不支惨状,因此他也向撒马尔罕的守军发出求援信,要求他们立刻赶来助战。接到总督的命令后留在撒马尔罕的伍麦叶军队开始大量出动,但其中真正的阿拉伯人依然只是少数,除了粟特辅助军外很多人都是临时上阵的奴隶,但他们的出现的确将突骑施人的注意力从前线吸引过来。为了收拾这支伍麦叶部队,熟悉本地情况的粟特流亡者向突骑施建议,纵火焚烧干旱草原。结果在风势的帮助下阿拉伯人惨遭火舌的侵袭,同时为了尽快与对手交战,阿拉伯武士们放弃稳健的步战,集体上马轰击突厥骑兵。结果在遭到数量占优的突厥-粟特骑兵反击后发现自己的退路也被大火所阻挡,最后除了有1000人逃出生天外其余万名士兵和奴仆都被突骑施消灭。利用城市守军的自杀性攻击,穆尔里成功将突厥人从自己这边吸引开,全军迅速从另一个方向靠近撒马尔罕。但考虑到对方骑兵可能随时返回,伍麦叶人也不急着迅速抵达,而是经常停下观察局势。
(七)当突骑施军队再次出现于自己眼前时残酷的战斗又接连发生三天,为了保护脆弱的辎重车队和家眷,穆尔里发动军中的奴隶也上阵杀敌。在战后获得自由之身的保证下伍麦叶军奴们使用最简陋的武器上场,用毛毯等织物充当临时护具,最后才逼退精疲力尽的突厥骑兵,顺利进入撒马尔罕。尽管解除了城市危机,但穆里尔的军队却伤亡惨重,各族部队与奴隶、家眷死伤多达2万多人,几乎是突骑施-粟特联军伤亡的一倍以上。在之后的四个月里伍麦叶人都只能留在城市中休整,慢慢补充受损的兵力。到731年的11月穆里尔还北上击退围攻布哈拉的突骑施军队,然而他已经意识到河中是一片难以据守的地方,决定将大部分部队再撤回呼罗珊待命。因此在这年冬季作为首府的撒马尔罕都只有800名伍麦叶守军留守,在之后的几年里阿拉伯人也再次失去对河中的控制。这一战的惨胜还给伍麦叶王朝本身带来负面影响,包括损失惨重的撒马尔罕分队在内,许多阿拉伯士兵来自靠近两河流域的东部地区。他们一直对叙利亚等地的西部同胞保有敌意与偏见,在他们撤回呼罗珊后就拒绝再次去往前线。后来推翻伍麦叶王朝的早期阿拔斯王朝军队就以这些人作为主心骨,伍麦叶人自己也不得不更加倚重波斯贵族,从呼罗珊等地招募波斯士兵。至于河中本身也因为这场战役而加剧损失,他们不得不开始寻求其他盟友,并因此接近大唐的西域驻军。为他们付出巨大代价的突骑施人也在736年被唐朝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破之后,很快从地区霸主的位置上被人拉了下去。
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
(一)古太白·本·穆斯林又有音译称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670—715),全名屈底波·伊本·穆斯林(穆斯利姆),也叫库泰拔·伊本·穆斯林。他是阿拉伯人,670年出生于今叙利亚(古称苫国),是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著名将领。深受哈贾吉·本·优素福的器重,曾被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委任为倭马亚王朝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军事扩张活动为阿拉伯帝国彻底征服中亚奠定基础,他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故死后被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奉为圣人。屈底波(库泰拔)早年是哈查只的部将,在担任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总督(埃米尔)后705年率军攻占巴里里,706-709年征服布哈拉地区,710-712年又率军征服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随后进军中亚的锡尔河流域,完全征服中亚地区,后为部将所杀。库泰拔是阿拉伯帝国在东线的主要将领,他对中亚地区的深入征服以及带领数万穆斯林进入中亚驻扎,使得伊斯兰教开始进入河中地区。696年伊拉克发生暴乱活动,总督哈贾吉被围,屈底波应募参加镇压有功,从此在哈贾吉麾下任军职并大受宠信。704年被哈里发韦立德擢升为呼罗珊总督,以木鹿城(马鲁)为首府。屈底波以哈贾只部属的身份,在呼罗珊统率的阿拉伯军队,共计有5.4万人(其中有巴士拉调集4万人,7000人是在库发调集的,沿途征募7000人,共有兵力5万余人)。701~710年间他连年出兵,先后征服位于中亚南部的吐火罗(巴里赫)、安国(布哈拉)和火寻(花剌子模)等地。

(二)712年屈底波又围攻河外的中心康国(撒马尔罕),康国被迫投降。屈底波进入撒马尔罕城,撒马尔罕居民被迫悉数从城内迁出,而后城内供阿拉伯人居住和驻扎。为方便穆斯林士兵礼拜在城内修建清真寺,主张宗教自由,并且允许穆斯林商人自由传教。屈底波军队继续远征锡尔河流域,压服石国(塔什干)、俱战提(列宁纳巴德)和渴塞(卡散)诸城。712年粟特居民在屈底波回师木鹿后起而反抗阿拉伯人,东突厥默啜可汗之侄阙特勤应当地地方贵族残余势力邀请率军入侵粟特地区,阙特勤所率之突厥骑兵尽占有阿姆河外诸地,只有撒马尔罕仍在阿拉伯帝国统治下。但在713年春屈底波利用突厥骑兵的困难,突厥骑兵从东亚草原远征至中亚地区,一路长途跋涉,因而已经是疲惫不堪。突厥骑兵虽然人多势众,但是突厥大军军心不一,胡禄屋、拔塞干、突骑施等部酋长各怀鬼胎,再加上一代名将屈底波的指挥。最终迫使突厥大兵撤离粟特,20万突厥大军甚至无力阻止阿拉伯军队向石国和拔汗那前进。根据阿拉伯史学家塔百里记载屈底波曾攻入喀什噶尔(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城),实际上根据考证这并非史实,而只是不可靠的传说。713年秋屈底波的军队在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唐称铁关或者呾蜜国)击败阙特勤率领的20万突厥大军,突厥大军一哄而散各回各家,胜利的征服河中地区。还在当年岁杪趁胜向东南进军到的喀什噶尔(古称疏勒,即今喀什)。接着在714年初春征服锡尔河流域,但未能攻克石国。

(三)在被征服的许多省区包括费尔干纳省也在其内都设置阿拉伯总督,阿拉伯人开始将中亚当做提款机,但是715年唐朝将领张孝嵩率领自己招募的杂牌军翻越葱岭讨伐西拔汗那、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率领五咄陆由突厥人组成的唐军从碎叶城南下,使得阿拉伯人又瞬间失去中亚,而这都是发生在屈底波被杀后的事。715年得知哈里发韦立德去世,由其弟心胸狭窄、妒贤嫉能的苏莱曼继承哈里发位。哈里发苏莱曼继位后开始运用国家机器实行“候鸟尽,良弓藏”、“狡兔死,功狗烹”的卸磨杀驴的政治政策,屈底波不耻苏莱曼为人,在苏莱曼继位前即与之素有嫌隙。屈底波素知苏莱曼的毒辣手段,于是决定先发制人,遂谋兵变。未果,为部下所杀。屈底波被杀后中亚诸国纷纷上表唐朝皇帝请求出兵打击阿拉伯人,唐玄宗在稳固政治后开始着手收拾安西的敌人,阿史那献被拜为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一路西征,很快击败盘踞碎叶城的胡禄屋部、穆斯林。唐朝定远道行军成立,目标直指收复中亚。同时拔汗那内乱给了唐朝打击伊斯兰势力在中亚的机会,张孝嵩率领1万唐军击败阿拉伯骑兵,吐蕃、拔汗那叛军、阿拉伯人被唐军斩杀甚多,x染红了河流。而阿史那献从北沿着葱岭南下,攻克铁关(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唐军前锋深入阿富汗地区,中亚各国纷纷杀掉残酷压迫异教徒的阿拉伯长官并出城迎接唐军。在米国国王狄瓦什梯奇的带领下与康国国王一起驱赶盘踞撒马尔罕的穆斯林,河中一带重归唐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