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经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作分享 |董百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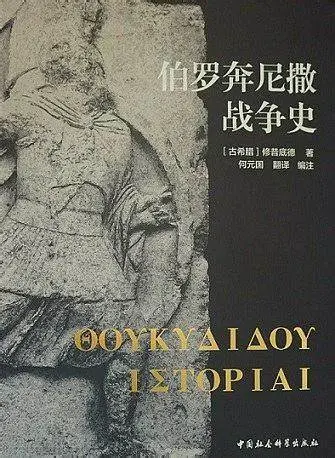

论瘟疫下的雅典人和雅典瘟疫的现实意义
思想的变化最终会决定了行为的变化,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于是将两者一起谈
人们首先陷入无助的绝望,原文是这么描述的“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自己身染这种疾病时,便陷于绝望之中,他们马上就会丧失一切抵御疾病的力量,使自己成为瘟疫的牺牲品。”[1]在那个科学和医学并不发达的时代,即使是小小的伤口,也可能因为感染或者破伤风而使人丧生,更何况是让全雅典城死去1/3人的瘟疫,可以谓是谈“瘟疫”色变。人的绝望一定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雅典人的绝望就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导致的。
严重的症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斯以精准写实的手法描述这次瘟疫的病症就花了整整几大段。那时的雅典城内简直就是一副死神蹂躏雅典城的灾难图画。
通常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发病原因。“健康状况良好的人都是突然地头部发高烧”[2]。由于医学水平的局限性,人们无法想象病毒细菌是如何传播,致病的,这也导致了人们的绝望,这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绝望和无助。
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人们还未能找到一种特效药,因为一种药物对一个患者是有益的,对另一个患者却是有害的,那些身体强壮的人不见得比身体柔弱的人更能抵抗这种疾病,所有患者都同样地死亡,就是那些采取了最好的防范措施的人也是一样的。”[3]修昔底德说:“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疾病,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的治疗方法。而医生们自己死亡最多,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触最频繁。任何人工技术都没有什么疗效。在神庙中祈祷...都同样的毫无用处”[4]
由于瘟疫,一部分雅典人开始对公序良俗和法律践踏
人们放弃了此前所沿用的丧葬仪式,把死去的人丢入火化堆中。有时看到别人已经堆放好的火化堆,就直接把尸体丢进去,即使同那个人素不相识。一些雅典居民也开始大胆越过法律,杀人越货,反正都得死,不如死之前尽情发泄。他们不畏惧法律的制裁,因为死神比制裁来得快得多。
一部分人失去信仰,他们对神不再敬仰,敬畏。他们最终认为信神跟不信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着周围的人全都无差别地被瘟疫夺取生命。
一部分绝望的雅典人想从神的身上找到瘟疫的起源和原因。在我看来,当人遭遇种种困难和苦难,巨大的变故和死亡威胁而束手无策时,再客观的人都可能模模糊糊相信起一种神意和天意来。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战争是否符合神的意志,人们也开始指责将领伯里克利。一群被瘟疫和战争压垮的雅典人甚至主张和斯巴达和谈,即使他们一开始是支持战争的。
命不久矣,及时享乐。瘟疫可不挑富人穷人,而是一视同仁。雅典城内的不少富人挥霍自己的财产,尽情享受最后的生命。在死亡面前,金钱只不过是一堆废物,丝毫阻挡不了死神的到来。
修昔底斯的记述对今天防疫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或启示
在预防疫情方面。就雅典而言,雅典城容纳了超出它所能承受的居民,加上城内卫生环境恶劣,居民用水是来自井水这类容易受到污染的水源,以上种种造成了瘟疫的肆虐。这启示我们城市规划需要多方考虑,除开经济和环境,还得考虑防范传染性疾病以及遇到重大灾难时的防范能力,不然等到灾难来领时束手无策后悔都来不及。
在抗击疫情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政府有力的管控。雅典人在瘟疫肆虐的初期开展积极自救,但医护人员因缺乏防疫护具而纷纷倒下,之后政府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去跟进,干涉。在新冠疫情初期,政府强有力的封控措施和派医疗队伍驰援武汉,很大程度的遏制住了疫情的传播和安抚人心。反观西方世界的防疫政策,由于体制原因无法做出有力的管控,属于是一开始就放弃抵抗了,宣传坐等”群体免疫“就等同于宣布政府的无能。
其次是科学的医疗手段。起初,雅典的医生们根本无法医治,因为医生们自己也不知道有效的治疗手段。反而因为他们和得病的人接触最多,所以他们死得也是最多的。有的医生到神庙去祈祷,而这种大规模的公共活动反而加剧了瘟疫的传播。看了这些文字,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位传奇的医生——伍连德[1],他曾被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采取科学的调查,隔离方式,最后扑灭了这场疫情。伍连德医生发明了伍氏口罩,把疑似病例隔离,用火车车厢隔离病人,大规模灭鼠,封城管控……伍连德医生的做法在新冠期间也得到了采用,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认为,伍连德不只是个技术人员,还有行政权,这对目前中国卫生体系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5]
不过,那时的雅典人和如今的我们所学所思都会受到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所以没[2]必要去嘲讽或者批评,我们只能从中吸收教训,总结经验,做好一切能准备的,大踏步不断前行。
[1] 来自伍连德_百度百科 (baidu.com)
[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译注 第二卷第七章51)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译注 第二卷第七章49)
[3]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译注 第二卷第七章51)
[4]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译注 第二卷第七章51)
[5] 来自 <https://new.qq.com/rain/a/20200220A07OBC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