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时代?不,是虚无时代,是竞争时代,是寻找自我的时代。

◼️ 《人物》杂志在今天发了一篇名为《考研时代》的文章。编者按中他们写道:“很难有哪个时代比今天更称得上是一个「考研」的时代。考研,甚至不再像是个人选择,而是一种集体趋同。人们期待靠这种最普遍的选择,找到人生的更多可能性。而考研这股风潮,也改变了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
◼️ 2017年,我参加2018届的研究生考试,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我穿的是灰色羊绒毛衣,为了不让厚重的大衣影响考试时写字的感觉,穿的蓝黑色的呢子外套;下午的英语考试被分配到一个奇怪的考场,椅子是歪的,桌子腿长短不一,一点点轻微的动作都会让它摇晃起来。于是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只能用大腿撑着桌面,让它保持平衡。考完最后一科专业课走出教室时,南方城市正进入到落日黄昏的时候,走廊被橘黄色的晚霞铺满,人群熙熙攘攘地朝四处散去。一瞬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复杂情绪。而那时的我却尚未明白,这一场日暮,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 2022年,无比艰难的一年。我躺在床上一边测着抗原,一边发出最后一篇23届的应试推文。五年时间,我与无数的考研学生遇见,看着她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却又踌躇徘徊,反复横跳在希望与自我否定的边缘。我听着她们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向我倾诉生活中的困难,同我讲:“考研是我唯一的选择”。希望、期待、憧憬,我们把考研当成是人才市场中的跳板,是简历上必须要有的一点经历,是内卷环境里的竞争力,也是不知自己去向何处而选择的安全区域。
◼️ 正因如此,我想我有欲望,也有资格谈谈过去五年间我所理解到的,考研的意义。
🫧
01/10/Tue.
虚无时代/竞争内卷
寻找自我的瞬间
@TuTouSuo™️
◼️ 虚无时代/空心病
我的大学过得特别没意思,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事情,无非就是一些闲下来就要开会、聚餐的社团,无数不想参加的班级活动,以及和一群朋友在大排档里拿着一次性塑料杯喝上一打又一打浮着白色泡沫的廉价啤酒,然后在早上六点躺在学校人工湖旁的草坪上睁开眼,摇摇晃晃地走回宿舍。
没有梦想。一点没有。
好像所有的能够提得起劲的事情在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就全部消失了。读了一个不需要太费力就可以拿到优秀的专业,身边也有三五好友兴趣相同,甚至大学和家就在同一座城市。当生活不需要我过多地消耗脑细胞,它就真的不再思考了。
所谓的人生意义、未来前途,都只在舍友报了会计和教师资格考试,好朋友开始学习商务英语、准备雅思,上一届要好的学姐拿到了保研资格或者出国offer时才会短暂地涌向浑浑噩噩的日子: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报名考试、暑假实习、参加更多的比赛和项目,为自己未来的简历增加漂亮的内容。
要比别人好,要和别人一样。在对未来的恐慌和不确定的状态下,亦步亦趋地做所有的事。但我还是不知道努力的意义在哪里,做这些事的目标在哪里,以至于几乎每一件事都没有太多的动力去认真地完成。
大学时我质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有目标、有规划,你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
「空心病」。北京大学教授徐凯文教授通过观察北大学生群体而提出的观点,是一种内心的空洞与精神的贫瘠,有着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患上「空心病」的人都被社会规则与他人的要求不断裹挟着,做着被普遍认为是好的、优秀的事情:
在学校里做乖学生、在家庭里做好孩子;中考、高考、实习、就业,每一步都由无数社会既有的经验组成——好的学历能够带来好的薪资待遇,能够拥有好的生活,可以遇到优秀的伴侣,实现幸福。但现实不是这样,每个不同的个体本应有着不一样的对于人生的愿景,哪怕今天有人说他想去流浪、去穷游世界,都是一种目标的体现。
可遗憾的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这么多的选择与岔路口,“康庄大道”永远只有一条,也正是那一条,那些别人眼中的「好与坏」,定义了每个成长中的青少年的世界观。而来自于他人的设定,来自社会既定规则的划分,自然无法完全得到承认,时常面临着自我的挣扎和反抗。我们都期待弄明白真正的人生意义,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欲望,却往往难以匹敌外在力量的挟持,导致自我的丧失。
不知道梦想为何物。就算挣脱了缰绳,也无法分辨自己要去的方向,甚至会回过头来,要求父母、老师、社会的规则,再为自己套上绳索:
告诉我,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只需要按照你们说的,考公?考研?还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获得幸福吧。
这是虚无主义的表现,也是虚无时代的缩影。
诺伦·格尔茨在讨论过往几个世纪中被持续辩证的虚无主义时认为,虚无本身是一种“无意义的意识形态”,是对精神世界的堙灭,使其既不认为自己所着手的、行动的对象和事物是有价值的,也不承认实在的物质生活本身的是意义,导致陷入自我怀疑与空洞的状态中去。
考研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是虚无的、空心的焦虑感催促着我寻找目标,而长期浸润于「考试升学制度」之下,缺乏独立自我认知的我能找到的目标,只有与就业相比更加稳定的、循序渐进的「考研」。
当时的我想,做只鸵鸟吧,把头埋到沙子底下。既然没有清晰的想法,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对未来的规划,那就让既定的那些规则、路径替我选择。继续待在象牙塔里,过熟悉的生活就好。
◼️ 竞争时代/内卷
「内卷」,最开始诞生于建筑学的概念。被引入人文学科后被认为是“大量的重复劳动却未能创造出更多生产价值的行为”。而现在,它已然是人才竞争、资源争夺、同辈压力与生存困境的重要代名词。
2017年,那时候这个词还未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视野。我只知道作为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就业时的选择少得可怜,教师、公务员、文职、策划运营之外,同届或上一届的很多同学,都去当了房地产销售,在碧桂园、建发这样的楼盘里卖房、养家糊口, 辛苦,不算太体面,但能够赚到比其他职业多得多的钱。
985、211高校的本科生都去卖房子了;在互联网大厂里做一颗优秀的螺丝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连一所公立幼儿园对应聘的教师要求都要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起步了。
在高等教育开放生源的当下,本科生,哪怕是优质院校的本科生都不胜枚举、多如牛毛;内卷的浪潮汹涌而至,年轻人能够获得的机会也变得稀少起来,资源的挤兑最后造成的,就是一块蛋糕不够分,好的工作很难能够落在普通学历、普通经历的人手里。
再加上疫情三年裁员、市场就业不景气,自然让更多的本科生选择深造,用研究生的头衔为自己博得一点点在就业中的优势。
很悲观地来看,很多选择考研的人,是已然无法从既有的学历、文化资本中获得太多的成长的可能,无法为现状所满足,才开始思索,如何让自己更加接近理想中的生活。
换句话说,研究生头衔为我们这些没有先天优渥的家庭背景,对现状也难以妥协的「小镇做题家」提供了多一点点的「自由选择」的机会,让眼前的路不再是单行道,而能够多一些的、改变命运的分岔路口。
没钱、没机会,就只能依靠这制度化的路径,一条最明显的、最有方向的路径,通向更大的世界。
◼️ 成为研究生后/会改变吗
2017年到2022年,5年时间。我终于可以回答当初那个问题:“你的目标是什么。”
也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开始在考研这条路上摸索,努力去尝试很多自己所喜欢的工作——记者、撰稿人、老师、活动策划、内容运营。最后我明白,目标永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你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不断浮现出来的剪影,是你越向前走,越能够去清晰描绘它的轮廓和具体形象的过程。
考研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大学之前的所有阶段性的选择都是由整个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中考、高考、大学——那么考研,就是由我自己,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所选择的对象,也是我第一次,不受任何其他人的监督、要求,自主地坚持下来的一件事。而后,我才能够继续,去追逐其他的想法,去拓展更多的视野。
虽然这一切不是全部由考研所决定的,但它是一切的开端。
于是,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由橘黄色晚霞铺衬的傍晚,走出教室的刹那。我想起博尔赫斯的那句话:
/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
/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
/人们彻底明白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
写到这,我竟然很想回去,拥抱2017年的那个穿着灰色毛衣的女孩。我不会告诉她未来五年的故事,我只想去抱抱她,谢谢她矢志不渝的坚持,谢谢她,让我看到如此令人沉醉的霞光。

⛄️
* ᴳᴼᴼᴰ ᴺᴵᴳᴴ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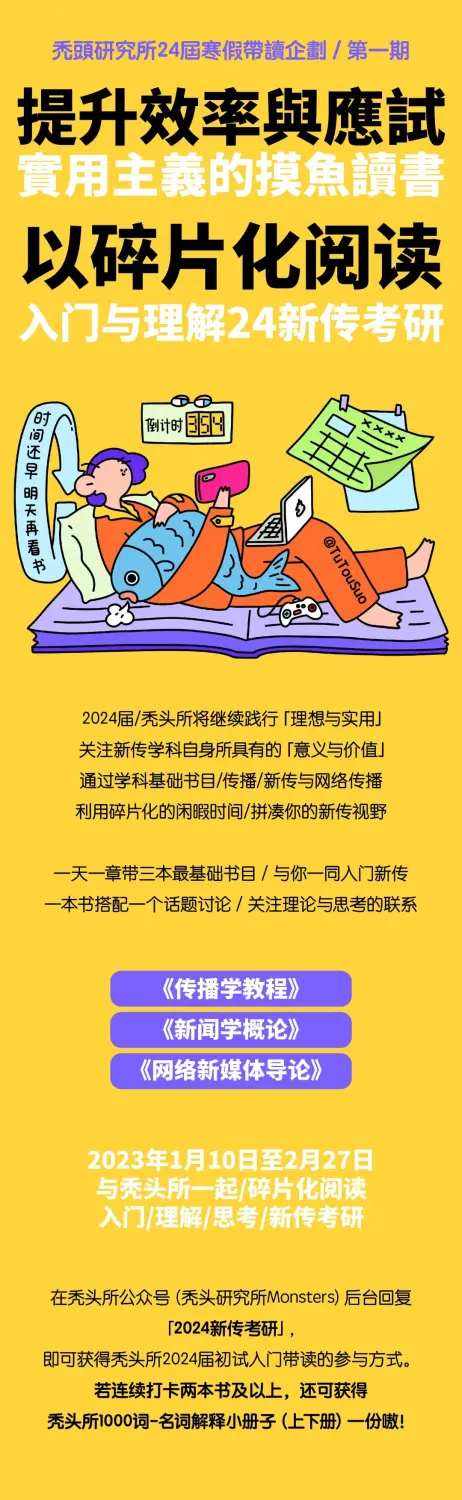
「2024/TuTouSuo」
✧
追逐自我/畅意自由
保持灵魂对Freedom的渴望

「2023/TuTouSuo」
つ♡⊂
将书籍与宇宙一同
随身携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