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巴里斯坦史》英译本序
翻译自《直到伊历613年(1216)的塔巴里斯坦史节译本》(A Abridged Translation:The History of Tabaristan,compiled about A.H.613(A.D.1216),后文统称塔巴里斯坦史)
巴哈丁·穆罕默德·本·哈桑·本·伊斯凡迪亚尔(Bahā’ al-Dīn Muhammad ibn Al-Hasan ibn Isfandiyar,俗称伊本·伊斯凡迪亚尔)著,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Edward Granville Browne)译,1905年英译本
这序没意思啊,就介绍了那么两三个学者[doge]

我翻译该书的目的并没有那么宏大,即使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也还是担心没有达到我的期望。一开始我并不是想在塔巴里斯坦史方面有所建树,只是想着为我正在编纂的《波斯文献史(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第二卷找新的史料。虽然我们还远没有达到那种掌握了充足的史料记载,并敢肯定已经没有漏掉什么重要性史实的地步,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对波斯人的精神生活和哲学发展进行教条式的或概括性的描述。学习波斯语的学生往往要学上几个月才能翻阅波斯史方面最重要、不可或缺的历史著作,如拉施特(Rashīd ud-Dīn)[1]的《史集(Jāmiʿ al-tawārīkh)》、志费尼(Juwayni)[2]《世界征服者史(Tārīkh-i Jahāngushāy)》;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可以利用可能出现的机会,熟悉那些很少阅读的地方史和特别的历史的内容,其中的一些可以在“穆罕默德手稿”这个庞大的收藏系列中找到,这些地方史和特别历史能够不断提供在大型通史中所缺少的有价值的细节以对历史进行说明。
[1] 全名为Rashīd al-Dīn Ṭabīb或Rashīd al-Dīn Faḍlullāh Hamadānī(1247-1318)伊尔汗国大臣、著名史家
[2] 即Atâ-Malek Juvayni (1226–1283),伊尔汗国大臣、史家

学者们在搜集手稿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俄国学者,为波斯的里海省份——吉兰与马赞德兰提供了完整的史料来源。1850-1858年间,多恩(Dorn)[1]在搜集手稿方面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首先是他的《Geschichte Tabaristan‘s und der Serbedarenach Chondemir》;接着便是他搜集的四卷著作:
一、扎希尔丁·马尔阿什(Sayyid Dhahirud-Din al-Mar‘ashi)[2]的《直到1476年的塔巴里斯坦、鲁扬与马赞德兰史(history of Tabaristan,Ruyan and Mazandaran,composed about A.D.1476)》
二、阿里·本·沙姆苏德丁(Ali ibn Shamsu’d-Din)的《吉兰史(History of Gilan)》,亦称《汗尼史(Tarikh al-Khani)》,该书续马尔阿什书直到1514年;
三、伊布努·法塔赫·福曼尼(Ibnu‘l-Fattah al-Fumani)[3]的《吉兰史:1517-1628(History of Gilan (from A.D.1517—1628))》
最后,是他搜集的二十二位阿拉伯和波斯作家的著作节选集,他们偶然谈到了与里海诸省有关的问题。
同时,我在准备编纂《波斯文献史2》时所发现了另一本极具价值的著作:梅尔古诺夫(Melgunof)的《里海的南岸,或波斯的北部省份,莱比锡,1868(Das sudliche Ufer des Kaspischen Meeres,oder die Nordprovinzen Persiens,Leipzig, 1868)》。(俄国学者)即使只是对马赞德兰方言进行研究,其成果也比研究波斯其他地方方言的成果大,特别是在上述两位俄国学者的努力之下。
[1] 即约翰尼斯·阿尔布雷希特·伯恩哈德·多恩(Johannes Albrecht Bernhard Dorn,1805-1881)亦称鲍里斯·安德烈维奇·多恩(Boris Andreevich Dorn)德国东方学家,曾在哈雷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语言学,后在哈尔科夫大学任东方语言教授,1835年任教圣彼得堡大学,移居俄国。主攻方向为伊朗语言学与里海地区历史
[2] 即Zahir al-Din Mar'ashi(1412-1489)塔巴里斯坦本土史家,出身圣裔(Sayyid),身份高贵
[3] 亦称Abd al-Fattah Fumani,17世纪吉兰省本地史家,fumani来源自吉兰下属的fuman城


(由于地理上)高耸入云的达马万德峰(the Great Cone of Damawand [Dunbawand])与其所属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将里海诸省与波斯本土分隔开来,因此里海诸省与波斯相比在历史和其特点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差异。即使萨珊王朝已经灭亡,伊斯帕巴德王朝依然在继续铸造着巴列维货币,在塔巴里斯坦的深山老林中坚持着祆教信仰,他们与阿拉伯人的争斗直到838年卡伦家族的“勇者(gallant)”马兹雅被阿拉伯人俘虏并残忍处决方告结束,马兹雅是文达·胡尔穆兹之孙,卡伦之子。不过25年后,宰德派的圣裔在当地建立了什叶派的统治,直到928年;之后便是齐亚尔王朝的统治,其中沙姆斯·马阿里·卡布斯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即使遭受过了灾难般的蒙古入侵后,古塔巴里斯坦贵族的代表仍然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

对于这个陌生而有趣的国家,每一个来过的旅行者心中都必然留下了最清晰、最难以言喻的回忆。1888年秋天,我从波斯回家的路上,花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翻过厄尔布尔士山,没有哪段经历能比我的这段旅程更加生动、深刻了:首先从伊拉克·阿贾姆的石质平原进入阿格(Agh)的低山,那里有潺潺的溪流和几乎英国式的树篱(hedge-rows);蜿蜒而上,到达雄伟的达马万德峰的东侧;拉尔(Lar)的幽深峡谷(canons);如勒内的阿尔卑斯山一般的美景;往下走,穿过岩壁山谷,进入原始森林,野生石榴的红色花朵闪闪发光,并覆盖着蕨类植物和苔藓;海岸的沼泽地区溪流缓缓,池塘静滞;悠长的阿穆尔河上建有一座小桥;巴夫鲁什(Barfurush)[1]城与谢赫·塔巴西(Shaykh Tabarsi)[2]的沼泽农田,在巴布教的历史上值得纪念;当然还有里海沿岸大片大片的沙地。
[1] 今巴伯勒(Babol)市,位于马赞德兰省中部
[2] 即谢赫·塔巴西陵墓,位于马赞德兰省。1848年巴布教徒与伊朗王军爆发了一场战斗(Battle of Fort Tabarsi)

说回本书的原作者——穆罕默德·本·哈桑·本·伊斯凡迪亚尔(通常为简洁起见称为伊本·伊斯凡迪亚尔),他是已知最早撰写成系统史书的一位历史学家,其著作已流传到我们的手上。关于他的生平,除了他自己在作品开始时告诉我们的以外(下文第3-4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他所提及的供他写作的一些史料来源——特别是《巴文德家史(Bawand-nama)》和阿布·哈桑·穆罕默德·亚兹达迪(Abu‘l-Hasan Muhammad al-Yazdadi)的《乌古德书(Uqud)》[1]——如今似乎失传了。多恩根据《扎希尔丁的塔巴里斯坦史(Sehir-eddin Geschichte von Tabaristan)》得出公元1216年作为他写成本书的日期,也就是说,比扎希尔丁早260年;因此多恩认为:扎希尔丁十分“自由”地利用了他的著作。这种利用可谓是随心所欲(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看上去简直就是完全的抄袭(不过在波斯文学中,这一点可谓是司空见惯了),这将会使出版伊本·伊斯凡迪亚尔的原著成为一部超出分外的工作了。不过嘛,我认真地想了想,我弄出一个本书简略英译本,可能也有它的用处。它没有别的作用,就是可以让其他波斯语专业的学生避免阅读原文的麻烦,或者使学生免于(因为看的很吃力而)只从书里得到了失望。
[1] 只能知道书的全名叫《Oqad-al seḥr wa qalāʾed-al dorr》

然而,最好的翻译并不能取代一篇好的原作,只有出版一部完整的、经过仔细整理的原著就可以被视为一部最终的、决定性的作品;因为,即使译者拍着胸口保证他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已经完全理解了作者的意思,这种自信读者也体会不到,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原文;这种反对意见对像现在这样的删节或缩减译文的影响更大,因为根据译者的个人偏见和倾向,缩减的过程肯定是不均衡的。例如,对我来说,能为波斯的文学史或私人生活史带来新的发现的片段都是极具价值的;而那些反叛王公和统治者的战争,只要能判断出来,仅仅是出于个人野心而不是出于民族或宗教的冲突或理想,就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因为与战争无关任何基本的对立。例如,所有与马兹雅有关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最高利益所在,因为他坚持旧的波斯民族和宗教理想,而从标志着塞尔柱权力衰落的王公内斗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基本原则,只不过是令人厌烦的无关细节的列举。然而,对于另一个从不同的角度——比如军事或政治方面看待波斯历史的人来说,我认为无关紧要的这些问题看上去就十分重要了。

在序言里我还要多说几句。印度事务局图书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的做法和其他几个大图书馆的倒退、愚昧的想法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得益于其开放性,我有幸读到了这本相对来说还是挺罕见的著作,这本著作是波斯语学生不能忽视的史籍。在我阅读的时候,我会努力从中提炼出所有我感兴趣或重要的东西,以便为我所用。这本英语节译本我原本是无意出版的,但在年迈的简·吉布(Jane Gibb)夫人的慷慨资助下,这本节译本被选进了“吉布纪念丛书”,由Jane Gibb夫人建立的这个丛书基金会不仅是为了纪念她儿子[1]渊博的学识与一心一意的研究精神,而且还是为了延续他所热爱的事业,与坚定的推进他孜孜不倦想要追求、达到的目标。该基金会出版的有关西亚和中亚历史的作品之多,使得这类书籍在英国首次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盛况。在这种情况下,经基金会其他董事的同意,我决定将这份原本只想供我个人使用的节译本交由出版社进行修订。大英博物馆的A.G.埃利斯先生(Mr A.G.Ellis)[2]给予了我最慷慨和最宝贵的帮助。在我看来,他在穆斯林文学及相关书目方面的学识在当时在世的欧洲学者中可谓是举世无双;尽管他工作繁重,闲暇时间亦不多,但在这本书付印之前,他几乎已经读完了每一页;对他来说,我不仅要感谢他在姓名首字母后添加的大量脚注,还要感谢他在第271-280页上的意见,使我纠正了许多本来会有损这几页正确的错误。在此,我对埃利斯先生给予我的诸多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1] 即伊莱亚斯·约翰·威尔金森·吉布(Elias John Wilkinson Gibb,1857-1901)苏格兰著名东方学家,以其浩瀚的手稿收藏著称,但44岁时死于猩红热。死后其母亲建立“吉布纪念丛书”,致力于翻译中亚、西亚的原始著作
[2] 叫这名的人很多,最有可能的是这位:Alexander George Ellis(1851-1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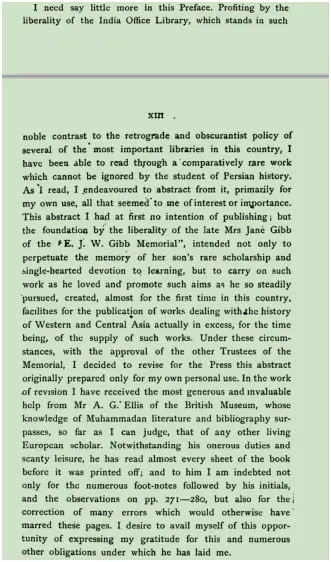
对于索引(本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可谓是下了大功夫。在索引的帮助下,我想研究波斯的学者们都能轻而易举地在文中找到他希望查到的任何一段文字了,这不仅可以用在印度事务局图书档案馆里那些作为我著作基础的手抄本中,同时也可以用来应付手头上的其他手稿;此外,某些名字会经常出现【像什么穆罕默德、哈桑、阿里这些】,如果塔巴里斯坦史方面的知识没有我那么精深,往往很难确定其身份问题。因此,为了应付各种有疑问的情况,我都在这些人名后面放了一个罗马数字,表示这个人大概活跃在公元多少世纪。
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
1905年五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