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网络文学研究的原生理论》崔宰溶 著

网络文学研究的原生理论
[韩]崔宰溶——著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丛书
作者:崔宰溶
责编:冯 巍
定价:56.00 元
内容简介
通过与西方相当不同的独特途径,中国的网络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网络文学在规模上的巨大膨胀和各种媒体的热烈关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得到迅猛发展,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本书从网络文学研究面临的现实困境入手,寻找到“原生理论”和“网络性”两个突破口,对21世纪以来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已有的得失做出分析评价。
作者认为,2011年以前的网络文学研究侧重于对“作品”和“学术理论”的研究,二者都与网络文学的真相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往往只看网络文学的“结果”而不看其“过程”。但仅仅从其“结果”出发,我们很难把握其实际的运作模式。网络文学只有在使用者的实际“经验”当中才能够存在。通过分析网络文学“原生人”(the vernacular)的语言,作者探讨了其作为“原生理论”的意义,认为网络文学的原生理论家所持有的“爽”的文学观具有一种积极的自我辩护逻辑。这些原生理论家对网络文学的运作模式拥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虽然网络文学的原生理论不能全面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分析,但作为一种反省具有独特的参照价值。
作者简介

崔宰溶,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韩国明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近几年专注于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中国网络小说的韩语翻译》《智能手机时代里网络文学的变化》《小说的再媒介与后人类的出现》等,并将古龙、韩寒等中国作家的书译成韩文。
图书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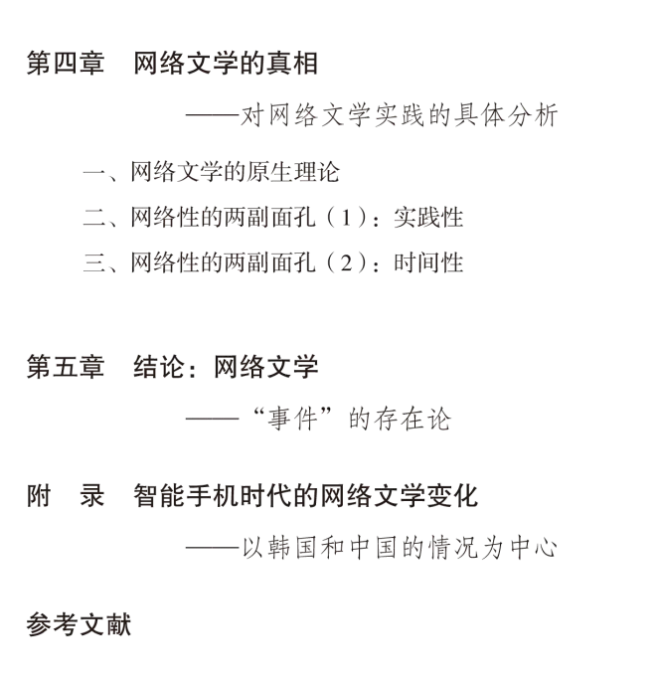
内文试读
结论:网络文学
——“事件”的存在论
本书从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既有成果出发,对它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并提出一些意见。在研究过程当中,我发现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基础,无论是有关理论的介绍和讨论,还是对主要作品及其作家的分析,都获得了不少成果。超文本性、民间性、后现代性、互动性等主要概念已被广泛地接受,变成了学界的常识。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研究有几个共同性问题,诸如对西方理论的盲目接受,对“作品”等一些传统文学观念的依赖,研究的抽象化、观念化倾向等。面对此问题,我试图通过“原生理论”和“网络性”两个概念来突破既有研究的局限,进而对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进行具体分析。
我认为,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
1.克服西方理论的盲目接受和滥用现象。依据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本书对超文本、后现代主义等主要西方理论概念进行了批判性考察,纠正这些概念在中国的滥用现象。
2.在网络文学研究中首次介绍、使用“原生理论”概念,揭示网络文学使用者的文学行为拥有的具体文化含义。
3.提出“网络性”概念,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网络”,摆脱以“作品”为代表的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
在本书中,我介绍和梳理了国内外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主要概念下了定义。我主要探讨了兰道、亚瑟斯、博尔特等主要西方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并介绍了“超文本”“网络文学”等核心概念及有关论战。我对中国网络文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现,研究中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现象比较严重,对网络文学的态度也有不少问题。本书成书之际距离我最初提出这些问题,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我认为我发现的这些问题当前还是有意义的。
随后,我试图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已有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问题。第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问题。我指出,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历史性的、冷静的态度。第二,抽象化、观念化问题。依我看,西方理论中所涉及的网络文学和中国的网络文学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但大部分中国研究直接沿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国内网络文学现象,结果导致研究的抽象化、观念化。第三,网络文学的“自由”问题。中国的研究一般过于夸张网络文学的“自由”,但对现实的具体考察则证明网络文学的自由是有限制的。第四,后现代问题。目前几乎所有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都使用“后现代”概念,但这一概念本身是可疑的、模糊的,并且中国研究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太抽象、不符合现实。第五,传统文学概念对网络文学的束缚问题。我认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些传统文学观念对网络文学造成不必要的束缚,阻碍我们对它的正确理解。
在第三章,我提出了本书的两个主要概念:“原生理论”和“网络性”。原生理论是某一种(大众)文化的原住民自己的理论,它所强调的是对其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力。这一概念不仅让我们看到大众拥有的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且将大众的思维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我认为,网络文学的使用者往往表达出他们的原生理论,他们对网络文学的理解、他们拥有的有关知识是局外人难以比拟的。他们不是文化产业的受害者,而是该产业、该文化的使用主体。“网络性”则指某一(超)文本或某个人的(文学)行为在网络中所获得的独特意义。通过这一概念,我们能够克服“作品”“文本”“超文本作品”等传统概念的局限,把握网络文学的流动的、运动的状态。在网络中,网络本身优先于作品,而网络使用者的写作、阅读等所有文学行为都是建构“网络”这一空间的活动。“网络性”概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鲜的研究角度,使我们看到网络这一新文学空间中发生的文学现象。
这些概念和理论,如果与中国网络文学的实践搭不上关系,就没有意义。这就是我在本书里一直强调的观点,所以在第四章中我利用这两个概念对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第一,我分析了网络文学原生评论的语言,探讨其作为原生理论的意义。我认为,网络文学的原生理论家所持有的“爽”的文学观,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辩护逻辑,是名副其实的原生理论,他们对网络文学的特征及其商业性运作模式拥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虽然网络文学的原生理论不能全面取代主流研究,但作为对主流研究的反省并使其局部妥协,还是有巨大意义的。第二,我从网络性的两个不同侧面,即“实践性”和“时间性”出发,分别分析了其在实际网络文学中的具体表现。首先,对“实践性”的研究。对“穿越小说”的分析证明,网络文学是形成身份认同感的主动的实践;对粉丝活动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中发生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复杂博弈过程,在这里“作品”的垄断地位被摇动,使用者的活动越来越重要。其次,对“时间性”的研究。对“挖坑”现象的探讨告诉我们,网络文学是随时应变的存在,因此对它的评价总是一种“断章取义”;对“剧透”现象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作者、使用者、网络上的超文本之间发生着一个复杂的时间性博弈过程,而网络中的时间性是与以前的媒体的时间性有明显区别的。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网络文学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种“状态”或“过程”。所以,网络文学一旦离开网络就会变成另一种东西,我们只能将它放在网络中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它。
在网络文学实践中,读者的参与度比以前远远提高了,读者不仅阅读文本,而且还构造出他自己的“数据库”、发表评论点评、推荐或批评特定的作品……每个网络使用者的经验都是独特的,正如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具有独特性一样。在文学网站中,使用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使用者、实践者,他“生活”在其中。也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性文学的开端。
以前的网络文学研究侧重于“作品”和“理论”的研究。很遗憾,这两者都与网络文学的真相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往往只看网络文学的“结果”而不看其“过程”。但仅仅从其“结果”出发,我们很难把握其实际的存在方式。网络文学只有在使用者的实际“经验”当中才能够存在。
尼采说,“闪电”不存在,唯独存在的是打闪电的“行为”本身。这个行为背后并不存在任何“实体”或“主体”。
因为,就像人们把闪电(lightning)和其闪耀(flash)分开,把闪耀当作一种行为(action)、叫作闪电的主体所引发的一种效果一样,大众道德(popular morality)把力量和力量的呈现分开。……“行为者”只是被编造出来,然后附加于行动上的——行为(the act)就是一切。
那么,准确地把握闪电可能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作为实体的闪电根本不存在。网络文学也一样,它只有文学行为存在,而我们能够对它下定义且进行分析的“实体”根本不存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实际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网络文学的历史中,没有永恒不变的存在。个别的文本在不断的时间和实践当中有时获得新意,有时被彻底遗忘。文本和文本之间、文本和使用者之间、使用者和平台之间,甚至平台和平台之间,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博弈,而这个博弈的过程就是网络文学的闪电。离开了闪电,就没有闪耀。没有“网络”,就没有网络文学“作品”。网络,就是网络文学。
这是一种思考方式的转变,是一种由“名词性”世界观向“动词性”世界观的转变。众多著名网络文学“作品”,其实是以一种“动词性”的状态飘逸在网络当中。也许,这就是德鲁兹所说的作为“事件”(event)的存在。在这一世界观下,运动、关系、经验比实体、本质、分析更加重要。当然这还是让人比较陌生的思考方式。无论是学者或者粉丝,我们的注意力更集中在“名词性”的活动上:我们喜欢确定对象、对它下定义并进行分析。在这里,我不想否定这些“名词性”“实体性”的存在论,实际上它是我们的整个逻辑的先决条件。也许为了客观的研究,这种学术性的、逻辑性的思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客观是不是主观的一种特殊形态?没有亲自经验过网络文学这一“事件”的人,会不会对它做出准确的评价?这确实是一种“绝境”。
编/柳嘉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