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死亡报告:1931年
本篇目旨在对1931年身死的日军做简易的汇总。
参考数据来源:日本《官报》
图片来源:《一亿人的昭和史》、1932/1933年《满洲事变写真帖》

近期在整理日本官报的数据,因此就1931年9月18日-12月31日日军死亡情况作以简要的介绍。注意,《官报》数据仍可能存在部分缺漏,但比例不会太大。并且本文未计算伪军的伤亡。因此在战争初期选择投降的熙洽主导的部分部队和辽宁的张海鹏省防军的阵亡人数均未算在其中。
关于1931年战斗的介绍: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在东北的战斗部队和非战斗部队共十八万人,日军的战斗部队约一万人,另有在乡军人两万人,截止12月增调多支部队,战斗部队将近五万人。
然而,状似优势东北军严重分散在东北三省中,日军则集结于所谓“南满区域”,在局部区域如奉天及以南区域构成了优势,尤其是奉天,几乎处于日军包围之下,这最终导致开战时最强力的驻扎于辽宁的张学良嫡系部队处于不利地位,守卫薄弱的东北军政中心奉天一天内丢失,而张学良的不作为和国民政府的消极建议更是加剧了这部分部队的问题,使得虽不足以对垒,但能产生迟滞作用的精锐部队没能发挥作用。
事变爆发后,东北地区部队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指挥和协调,长期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而阵地战水平薄弱的东北军留守部队却多次选择对垒,在精锐的日军面前付出了惨重损失。辽宁方面的张学良嫡系部队被迫服从命令,撤往锦州,吉林方面,亲日派熙洽及其手下不少亲日派军官所部选择投降日军。两省部队各有一部分处于观望或者举棋不定的态势,其中相当部分在11月或者1932年才正式开始进行抗日行动,最终形成冯占海、李杜等自卫军力量。
兵力最少的黑龙江省,在马占山的统帅下,结合兴安屯垦军等部进行了江桥抗战,以三万名步骑部队对战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六千人和伪军张海鹏省防部队数千人,虽最终伤亡和失踪万人,但迟滞日军两个星期,毙、伤日军500余人,日军另因长期低温作战冻伤1000余人(如此大规模的冻伤,日军在当年和后期的总结中均认为是非常不值得的损失),并毙伤、击溃伪军数千人。为1931年战斗规模最大,战果最佳的一战。

自九一八事变到12月31日,日军迅速侵占了辽宁省和吉林省大部,以及黑龙江省小部分区域。在这一期间,日军先后在北大营、南岭、宽城子、江桥、“南满铁路”沿线各地进行了大大小小的作战行动。作为抵抗一方的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统一指挥和协调,且部分部队早在战前其指挥官就已经与日本勾结,导致在1931年实际投入抵抗者极少,但在各自为战地抵抗日军中的作战中,也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到12月,由于处于极端被动和缺乏指挥的状态下,位于东北的各军难以组织行之有效的大规模抵抗,除了南岭、宽城子和北大营三场事变当天和第二天的应急回击,以及11月初的江桥抗战外,大部分均为骚扰和局部的作战,且主导者成分庞杂,包括正规军和自发组织的民兵。由于日军本身没有制造过多的交火机会,因此1931年并不算是“喧闹”的一年。东北真正的大规模、全面性的抵抗,大体爆发于1932年。

根据日本《官报》登载的战死者名单,1931年不足四个月的时间中,日军有251人死亡。
其中:4人病死、1人自杀、246人战死或伤死。
然而,1931年日军实际伤亡来说,死伤并不能完全呈现几比几的比例。譬如北大营之战,日军虽然仅阵亡2人,但有十余人负伤,随后在沈阳城内的清剿行动也有多人负伤。当时的作战中不乏仅伤而不死的情况。即使是江桥抗战,第一阶段在大兴的作战日军共阵亡46人,但负伤者却将近两百,而在江桥抗战结束后,更是有1000名日军冻伤。导致当时参战的六千名日军实际因为死伤冻伤减员了五分之一之多。因此,仅仅从阵亡人数上不能完全判断当时日军付出的损失。然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许多战果。
在因战斗死亡的246人中,11人属于炮兵,2人属于陆军航空兵,11人属于骑兵,2人属于宪兵,5人属于工兵,其余均为步兵(包括数名文职人员)。

日军1931年阵亡者基本没有佐官(事实上,当时关东军,即使加上来援的部队,佐官人数也少的可怜),但包括许多尉官等。择选其中准尉及以上者列出,按照日军规定,战死者和伤死者等,都会追晋一级:
川野宽市(骑兵大尉):
隶属于关东军自动车队。11月19日死于齐齐哈尔南方十五里屯,死后追授骑兵少佐。一说此人为辎重兵少佐。
仓本茂(步兵大尉):
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9月19日死于南岭战斗,死后追授步兵少佐。
衣笠繁一(步兵大尉):
隶属于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步兵第七十八联队,11月19日,因在江桥战斗中负伤,死于辽阳卫戍医院奉天分院,死后追授步兵少佐。
板仓至(步兵大尉):
隶属于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11月27日,在北宁线绕阳河站附近死亡,死后追授步兵少佐。
前田冈孝治(步兵中尉):
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步兵炮队长,9月19日,在南岭战斗中死亡,死后追授步兵大尉。
井上友治(步兵中尉):
第二师团步兵第三十联队第一大队副,11月19日,因在江桥战斗中负伤,死于昂昂溪野战医院,死后追授步兵大尉。
吉泽留吉(骑兵少尉):
隶属于第二师团第二骑兵联队(当时仅一个中队),11月11日,在大兴屯西南死亡,死后追授骑兵中尉。
坂本健三(工兵少尉):
隶属于工兵第二大队,11月24日在腰高台子死亡,死后追授工兵中尉。
熊川威(步兵准尉):
隶属于第二师团兵第四联队,9月19日在宽城子死亡,死后追授步兵少尉。
芦田芳雄(步兵准尉):
隶属于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9月19日在南岭死亡,死后追授步兵少尉。
武者清治(步兵准尉):
隶属于第二师团步兵第十六联队,11月6日在大兴站死亡,死后追授步兵少尉。
奥村仁次郎(步兵准尉):
隶属于独立守备步兵第五大队,12月15日在平顶堡死亡,死后追授步兵少尉。

附录:亮眼战绩:
在初期日军部队集结最多的奉天(沈阳),最先自发抵抗的武装部队在19日奉天失陷后,仍然不断对其进行骚扰,义勇军事实上在1932年多次攻入奉天或者东塔机场。但早在1931年9月末,在奉天的独立混成第39旅团就多次遭到袭击。其中9月25日在兵工厂,第78联队的小山寅右エ门就被击毙,9月28日,第77联队的浦田元夫也被击毙。
11月4日,日军以第二师团第十六联队和野炮兵第二联队一部构成的嫩江支队在大兴站与马占山先锋阵地交战,中方以骑兵和步兵实施迂回打击,先头的第十六联队一个大队(由于是平时编制,战斗兵不足五百人)在11月5日遭到三面包围的打击,该大队坚守一夜,损失惨重,付出了一百余人伤亡的惨痛代价。相当于战斗力遭到了严重减损。整个江桥抗战后,日军参战的六千人伤亡五百余人,另有一千人冻伤,由于日军急于在锦州周边作战, 第二师团仅留少部分部队驻守齐齐哈尔,当时的日军评价,如果中方在此时向齐齐哈尔发起反攻,日方将毫无招架之力。然而,在江桥抗战期间损失三分之一的作战部队,消耗了巨量储备和精力的马占山方面,此时已经无力在短期发起反击,只能在海伦、克山等地修整,待第二年卷土重来。
江桥抗战期间日军独立飞行中队多次出动掩护和打击,针对中方部队集结点和炮兵阵地展开多次打击。马占山组织了步机枪进行防空,实际上导致参战日军飞机均不同程度受损,其中日军的航空兵中尉大针在一次防空中大腿被击穿,勉强将飞机开回了机场。在此后的多次作战中,几乎完全不具备成体系防空力量的东北军、义勇军等仍将对日军航空力量造成一次次或大或小的打击。
11月18日,日军第二师团针对齐齐哈尔马占山的最后一道防线进行全线总攻,后者最终在当天不支后撤。在此期间,位于日军战斗队形右翼后方的第三十联队会计部及其护卫部队遭到了中方骑兵的毁灭性打击,17人中有16人被击毙,仅一人逃出生天。事实上,会计部的这次覆灭经常被误认为是打到了第二师团总部,因为缴获了为数不少的日元。然而,实际被消灭的是第30联队会计部,但无论如何,规模虽小,这仍然是1931年少有的奇袭歼灭战。
12月30日,日军独立飞行第十中队一架飞机被击落,陆军航空兵曹长小野田义明和陆军航空兵军曹小川幸平均因此而死。

日军在1931年主要有三场大规模战斗,伴随如腰高台子、通辽、平顶堡、巨流河、蓝旗堡子、古城子等多次小规模战斗:
沈阳周边战斗(9.18-9.19),伤亡20余人(其中阵亡2人均在北大营)。
南岭、宽城子战斗(9.19),阵亡和续后伤死至少67人,负伤总计近200人。
江桥抗战(11.6-11.19),在三个阶段的战斗中,日军至少阵亡和伤死120人,负伤400余人,冻伤1000人。另外伪军亦伤亡数千人(10月期间的战斗无日军,为伪军主导的作战)
总的来说,按照估计,1931年日军的伤亡人数可能达到2000人以上,伪军亦折损数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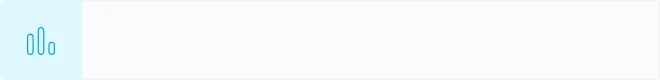
(备注:关于江桥抗战的日军损失,鄙人没有直接采用关东军或者我国书籍记载的数字,而是结合《官报》、日军各部报告,以及作战地图分析,并结合传统数据比较,进行核对取舍得到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