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人,要怎么发展?
今天专门从社会和文化认知的角度来谈一谈青年群体的发展困境。正如现在我们都能看到的,很多地方尤其农村三四线城镇依旧存在大量问题,发展不均衡,而这些地方的人,尤其是青年,正是更理应得到大众和舆论的广泛关注。毕竟,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就不存在所谓的“问题”,而遇到了无法解决感到迷茫的人,问题才是“问题”。

房子:在哪里扎根
房子,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哪怕是新生代,也大多坚持自己成家一定要有房。根据BBC的数据显示相比之下中国的新生代对拥有自己房屋的期望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

而在德国,甚至50%的人一辈子都不曾拥有自己的住房。抛开经济上的考量,即对于中国人来说房屋是最有效最大的投资,是最保值的不动产,所涉及的户籍学籍因素外,这一现象还有深刻的文化印记。
对中国人来说,至于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才意味着在身份上真正从属于那个地方,那个城市,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地方一份子和成员。这一点,不分城镇农村都是如此。比如若一人在北京上海打拼几十年仍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她/他就永远不可能被认可为北京上海人。有房是第一步。这背后反应的是深刻的农耕和宗族文化的印记影响,是一种偏静态和安定的思维;房子是基地、纽带,从此将人和地域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和族群关联在一起,而不是与之相反,会随处飘动,不确定的状态。换而言之,就是中国文化中深刻的“家“和”家庭“的概念,依旧是基于房子,养育后代为根本的,婚姻也是如此。虽然更西方化、现代化的思想正逐渐影响于青年群体,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文化思维的概念仍将保持深刻影响。

城市:压力不断增大
在当下中国以及其他快速发展国家的发展中,城市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一方面由于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红利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城镇生活和发展成本增加,从而逐步对城市居民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尤其对于年轻人群而言,融入城市并稳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主要原因为收入增加放缓,就业压力增大及住房压力的升高,个人对未来和收入的期许同实际的差别增大。 2013年,中国城镇地区住房自有率为89.22%,2002-2013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率城镇为4.15%,高于农村的3.55%[1]。在房屋问题上,城镇居民的压力要大于农村,事实上,某种程度而言,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得益于我国体制和政策,农村居民的土地所有权能够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因此即使在大量农民工进城后,如若遇到经济就业退潮不景气的情况,他们依旧可以退回农村,村里的土地和房屋就是广大农村居民最坚实的保障和最后的防线,这也是为什么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的原因,也是没有出现曾经英国为代表的资本化、商品化时期”羊吃人运动”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由于没有这样的条件和退路,这一压力就成为了极为沉重的负担,而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无形的绞索还在进一步收紧。
不仅如此,沿海地区特大城市基于自身区位优势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吸引而至,随着集聚经济而来的溢出效应使得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更加明显,从而使得次级城市发展困难,容易造成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以及“首市现象”(即首要城市的规模和发展远远超过其他的所有城市)[2]。这一点,在古代,以古罗马城为典型,将周边区域所有资源吸干,埃及北非的粮食,高卢日耳曼的奴隶,中东西班牙的金钱等源源不断输送进罗马城,整个帝国都围绕罗马的发展和顺利运转而提供资源,才成就了拥有百万人口的古代奇观(人口具体数量学界有争议);而在当代,则以南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为典型,尤为明显。这一现象,对于长期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而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罗马编年史》(Annals)还曾厌恶的嘲讽日耳曼人喜欢喝大麦酿造的散发出腐败气息的啤酒,甚至只需要通过气味就能判断出谁是野蛮人谁是罗马人-----对于罗马人来说只有葡萄酒才是精致的文明人的饮料;却绝不会料到正是来自这些“野蛮人”的一支,哥特人,最终将罗马城的荣光扫进了历史的尘埃。毕竟,如果“野蛮人”永远也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成为真正的罗马公民,那就用火与剑去证明吧。


思想:焦虑与迷失
当下中国城市青年拥有一种普遍性的焦虑,这种焦虑状态同城市的发展环境有关,也是文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化,每年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毕业,而这一数字比例还在不断上升,2017年本科毕业生接近400万人且本科生研究生比例为8:1[3],而出国留学人数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根据BBC的数据,2016年为54万人。
这样规模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群体为社会带来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然而年轻人群的特性则是独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良好的生活品质,追求拥有较少约束的生活环境,而与此对应的则是这些年轻人不能完全为社会所需要和消化;且最佳的上升阶段和机遇已经被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和不具备良好家庭背景的冒险家们所抢占控制,未来随着阶层固化的进一步收缩,希望愈发渺茫;因而年轻人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在精神上也感到空虚和迷茫,失去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期望,同时也没有信仰和信念作为生活的准则与支撑[4]。
这种背景下,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数量远超过社会需求的话,如果发生在社会建构不完善,没有足够变动能力的国家,就会造成政治和社会上的动荡和不稳定。比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中东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和消费市场是多么重要)。
这些问题和焦虑被年轻人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宣泄出来,尤其在青年文化上表现的特别明显,比如各类青年亚文化现象的流行;如此情形同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和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非常类似-----一方面加剧了社会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也具有潜在的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可能性,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对文化精神世界的渴求和对于新时期信念信仰的探索都是极其具有发展前景的,但需要合适的发展环境(亚文化现象往后会作为单独的主题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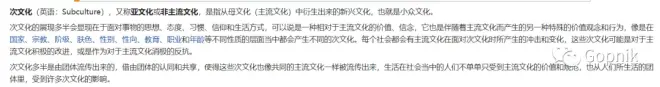

乡村:不理解、不适应
同集约化的城市相比,乡村所具备的竞争力非常低下,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而在乡土社会体系依旧完整的封建时期,中国独有的科举体系、宗亲体系与良好的乡村文化资源储备让乡村本身能够源源不断产出属于自己的高素质群体(只是描述事实),而这些高素质群体即使外出入仕经商,最终还会携带资本和人脉关系回到家乡,所谓“落叶归根”,在这样的循环体系下,传统时代的乡村得以持续保持良好发展。根据费孝通的研究数据,在清代,通过科举考试的学生中有41.46%都来自于农村[5]。这一点,在工业化商品化经济的今天,完全不成立了,村镇地区本地青年人不断离开并前往城市,导致社区空心化,同时更缺乏外来高素质青年人口的补充,由此造成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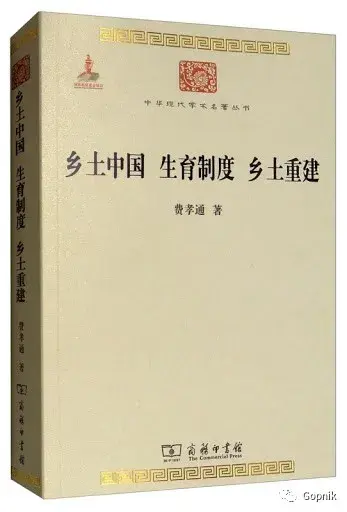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教育体系同西方类似,是一种外来的、欧洲式的、建立在近代化工业化基础上的教育体系,所教授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源于城市这一实体的,因而城市中所产出的文化思想是工业化,独立化,同乡土没有连接的。按照斯宾格勒的理解,城市是自由的,冷静的,脱离了土地的力量而理性变得越来越有力,城市里成长出来的人群是一种“智性的游牧民”[6],他们是漂泊不定的,是无根的,因此城市能够产出更多独立的,自在自为的思想意识,这种“智性化”的意识对乡村而言是陌生的,是生长在土地上的农民无法理解的,因而也是城市同乡村脱离分裂越来越厉害的重要因素。

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为城市的建设做准备的而非是为农村,尤其是在文化领域更是如此,因而当下的年轻人很难去在接受过教育后重新回到乡村去生活和参与建设,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意愿和热情,也无法在乡村中施展才能;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一书中也提到,年轻人无法找到一种过度手段作为桥梁,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家乡,没有这种桥梁,来自城市和工业化的现代知识和文化只能悬在空中无法融入乡土的土壤[7]。不仅如此,在长期来自城市化的教育灌输中,青年人所自发性产生的独立性的,理性的,自在自为的,抽象式的思维文化理念同需要紧紧依托于土地,从故乡的景色中成长起来的植物性的乡村文化是完全不同的,现代的青年群体已经很难去接受和适应乡村的生活环境了,最终的结果是,乡村不断的丧失青年人口,仅有的文化资源也因为缺乏继任者的传承和维护而不断朽败坍塌。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作为乡村的“脱源化”现象。

因此,年轻人何去何从,该如何发展?恐怕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真正可行通用性的解决办法。不过,不论有谁宣扬乡村好,要回归乡村过田园生活,牧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抑或是,一线城市好,前卫时尚充满机遇;年轻人在对于自身利益和发展上是看得很明白而现实的,文艺情调作为理想可以,灯红酒绿作为一时的释放可以,但眼下,对于大多数青年人来说。。。。还是现实一点。不然的话,国家也不会大力发展振兴二三线城市和构建中心城市群了。
参考资料
朱梦冰,李 实.中国城乡居民住房不平等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9:92-93
迈克尔.斯彭斯,帕特里夏.克拉克.安妮兹,罗伯特.M.巴克利,城镇化与增长:城市是发展中国家繁荣和发展的动机吗?[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1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八个一”组合拳加快 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806/t20180625_340929.html.2018-6-25.
惠海鸣,中国绅士 译者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01:6
费孝通,中国绅士[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01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中信出版社,2013.01.01;264-265
费孝通,中国绅士[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