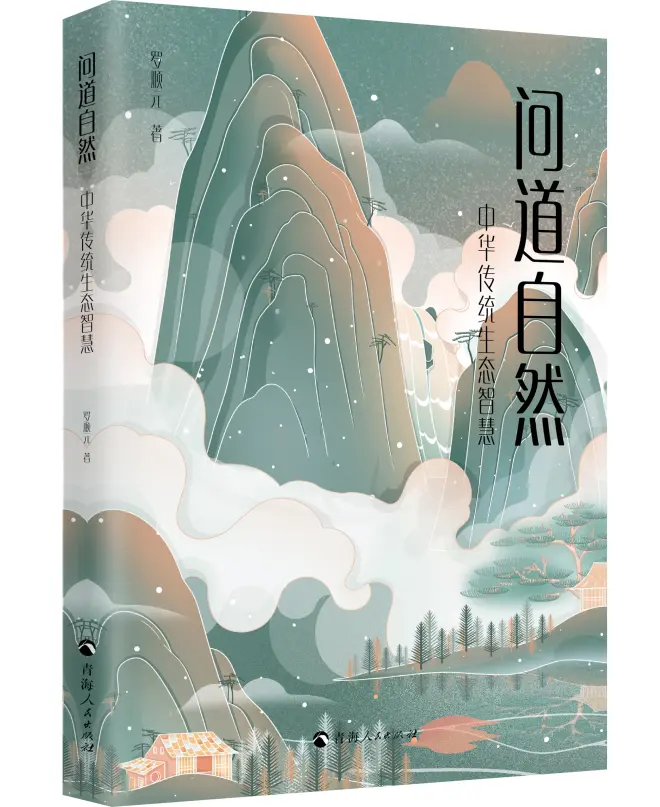罗顺元: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伦理观
儒家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主要体现为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伦理观,而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和正统思想,所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也就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伦理观,该思想的内容概言之就是:以人为本,热爱万物,和谐共生。
(一)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的提出
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的雏形。孔子是一位伟大的人本主义者,“仁”是他的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仁”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伦语·颜渊》)。孔子把人和人的价值地位看作是第一位的,《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起火被烧了,人和牲畜都有可能受到伤害,但孔子只是关心人而不问牲畜(马)。又,“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孔子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是,孔子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并不是西方文明所主张的那种人与自然是分离对立、人类要征服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向自然界的推广。
对于自然界,孔子主张“乐山乐水”、热爱大自然,拥有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情怀。《论语·雍也》记载:“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对于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山川河流等,孔子主张多了解认识,爱护保护它们。孔子叫他的学生学《诗》,以便多认识些鸟兽虫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对于好马,孔子称其有德,赋予人的品质,凸显出孔子对动物的关爱,“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论语·乡党》还记载了一个孔子及其弟子对山中鸟儿表示友好热爱的故事,“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意思是:孔子与其弟子在山中行走,遇见一群野鸡,抬头一看,眼色动了动,野鸡就飞起盘旋一阵然后又集体停在一处。孔子说:“山梁中的雌野鸡啊,时哉时哉!”子路也向它们拱拱手,接着这群野鸡振振翅膀又飞走了。孔子的生态思想,即使在现今社会也是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1988年1月,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呼吁:“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儒家亚圣孟子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即“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孟子,名轲,战国中期杰出的儒学大师,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儒家的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主张行仁政,以德治天下。在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孟子把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具体深化和阐明,提出著名的“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重视孟子的生态伦理观,他说:“属于孔子(公元前522—前479)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在人与自然万物的伦理关系中,孟子跟孔子是一脉相承,是一位伟大的人本主义者,主张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和睦共生的和谐生态伦理。
关于人之本性,孟子提出了著名的人性之先验“性善论”,即认为人的本性原本就是善良的。然后,孟子主张把人的善良的本质不断发扬光大,并且以自己为中心,由己及人再及物,把这种“善”推广到天地万物。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人性的善良,就好比水性的向下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人之所以会做坏事,是由形势所迫罢了。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人人皆有同情心,之所以说人人皆有同情心,道理就在于:现在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子就要掉到井里去了,每个人都会有惊骇、同情、怜悯的心情;这种心情是自发的,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不是为了获得好名声,也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声。人性的“善”是先验的,而且人人都具有这种先验的“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又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
在确定人性善良的本质后,孟子要求由己及人再及物把这种“善”逐步往外推。对天下民众,孟子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接着,孟子便把这种“仁爱”由人推广到天地间的自然万物,即著名的“仁民爱物”生态伦理思想。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宋代著名儒学家朱熹解释,“物”为“禽兽草木”;“爱”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语意解释得疏宽恰当、精练准确。这里的“仁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但不要“亲”,对“物”要“爱”但不要“仁”。“亲”“仁”“爱”是孟子“仁爱”观里价值等级由高到低逐渐降级的三种不同层次,这样孟子的“仁爱”思想便由对人的“亲、仁”逐步扩展到对万物的“爱”。这既是对孔子开创的“泛爱众而亲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针对墨家“爱无等差”主张的批驳。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一次,墨家的信徒夷之想去拜见孟子,夷之把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意即君王爱护民众就像爱护婴儿一样)理解为“爱无等差,施由亲起”(意即人与人之间并没有亲疏厚薄的区别,只是实行起来从父母亲开始),孟子对此进行了批驳、解释。“仁民爱物”这个命题正是对儒家之爱的进一步解释。正因为主张要“爱”天地间的自然万物,孟子对齐宣王不忍杀牛祭祀而赞赏,说这就是“仁术”;孟子接着感慨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不过,在人与自然万物的伦理关系中,人的价值地位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孟子的生态伦理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伦理,人本观念是孟子生态伦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孟子对于齐宣王恩及禽兽却没有行仁政关爱百姓表示诘问和不满,孟子两次反问,“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于统治者重视爱护马之类的动物却不管人民大众死活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抨击,“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
(二)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的发展与成熟
在孔孟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即“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之后,中国传统社会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上基本都是照此进行。在孔孟之后的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除了继承和发扬孔孟“仁民爱物”生态伦理观的核心思想外,在内容上还有一定的发展和扩充。
1.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在汉代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我们来谈谈汉代名著《淮南子》对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的发扬与拓展。《淮南子》撰写于景帝一朝后期,汉武帝即位之初被递交皇室,它以道家的老庄思想为主,同时吸取各家之长,兼收儒家、名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它集中体现了我国汉朝文景之治时的社会主流思想意识。《淮南子》的内容包罗万象,“宇宙自然,天文律历、阴阳五行、地理时令、世俗人生、治乱祸福、主术兵略、养生保真以及相关的诡异瑰奇之事无不罗列,有关哲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军事战略学等先民思想精华无不萃集”。东汉高诱说“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尽管《淮南子》以老庄思想为主,但由于它兼收各家之长,在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主张方面却与儒家的“仁民爱物”生态伦理观一脉相承。
尊重生命,爱护人类,以人为本,是《淮南子》生态伦理思想的鲜明主题之一。《淮南子》认为“蚑行喙息,莫贵于人”(《淮南子·天文训》),“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淮南子·精神训》),这也反映出了《淮南子》对人类自身的尊敬的态度,也为其人本思想做了理论铺垫。
《淮南子》的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淮南子》认为懂得人道和热爱人类自身是作为智者和仁者的必要条件,只要是缺少了关怀“人”自身这个因素,不管知道得再多,抑或热爱的事物再广,都不能算是“智者”和“仁者”。《淮南子·主术训》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又,《淮南子·泰族训》说“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智者”和“仁者”是为数不多的带有最高褒奖含义概念中的其中两个,是人们学习和修炼的理想境界,《淮南子·主术训》也如是说,“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又,《淮南子·泰族训》说“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现在,《淮南子》把对人类的关怀和热爱赋予并内化为这两个概念的必须内容,这就表明了《淮南子》思想中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取向。对于那种“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猒刍豢”(《淮南子·主术训》),不关爱人民百姓的行为,《淮南子》是深恶痛绝的,将其称之为“衰世”。
《淮南子》的以人为本思想,还表现为对人生命的敬重和珍惜,以及对占用身外之物的淡漠。《淮南子·精神训》说:“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使之左据天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由此观之,生尊于天下也。”这里说明了,人的生命是比拥有整个天下更珍贵的。又,《淮南子·诠言训》说:“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身体以生命为最高目的,金钱富贵只是附带的东西。
另外,《淮南子》还有天人感应的思想,即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相通的,是能够相互感应到的。当然,人对天的感应是常识,任何一种活着的生物都能感知周围的环境变化,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这里,主要讲的是自然之天对人的感应。《淮南子·主术训》云“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又,《淮南子·天文训》云“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上天能够感应到人,对人的不同行为做出不同的反应。一般说来,如果人们胡作非为,违背自然规律,祸害人民,损害天下苍生,那么,上天就会惩罚人类,降灾祸于人间或显示异常现象警示人们;如果人们至精至诚、遵守天道,那么也能感动上天,能得到天的帮助。总之,“天”是起着一种最终的赏善罚恶作用,是终极的是非评判者,是最终的正义行使者。
例如,国家政令失常,社会混乱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难或异常现象,“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淮南子·天文训》);又,“君臣乖心,则背谲见于天”(《淮南子·览冥训》)。如果违反自然规律,祸害天下苍生,就会自然灾害连绵不断,“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蜺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淮南子·泰族训》)。
而反过来,如果心怀天下,精诚守道,上天就会帮助人,降祥瑞于人间,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万物欣欣然,“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淮南子·泰族训》)。又,“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淮南子·主术训》)。那些精诚守道,全性保真的人,在个人遇到危难时,上天也会及时相助,“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济而波罢。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于天”(《淮南子·览冥训》)。而且,上天对人的感应没有身份地位的要求,只要人们诚心诚意、依循天道,无论身份地位贵贱与否都能感动上天。
在天对人的感应过程中,“气”是媒介,天正是通过“气”来感应到人的,“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淮南子·本经训》)。在《淮南子》中,能够与大自然相通并非人的专利,动物和其他自然物也能感动天,引起自然反应,如,“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蚕珥丝而商弦绝,贲星坠而勃海决”(《淮南子·天文训》)。客观地说,《淮南子》所述的天对人的感应现象是带有神话色彩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由于他把“天”定位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正义评判和维护者,执行着赏善罚恶的职能,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威慑作用,也能够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也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其次,我们再来谈谈汉代大儒董仲舒对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的继承与发展。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汉代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广川人(今河北省景县)。在中国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董仲舒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时代界标式人物。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是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历经秦代短暂统一的法家治国,到汉朝初年,虽然文、景帝崇尚道家的无为之治,但社会上的各个学派争鸣之势早已复兴。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其著名的《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此主张得到汉武帝的推崇和采纳,孔孟儒学从此便从诸子百家中凸显出来,跃居独尊的地位,成为了此后几千年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主干。另外,董仲舒吸收先秦诸子的正确思想,融入儒学体系,形成适应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新儒学——经学。董仲舒成为经学大师,“为群儒首”。他的思想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影响中国政治达两千年。虽然董仲舒的思想理论主要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但是,董仲舒是一位划时代的大哲学家,他的思想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一部分就论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董仲舒对孔孟的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除了继承和发展其本质核心外,在内容上还有新的拓展和增加。
董仲舒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观点是:人为天下贵,对于自然万物,人应当遵循天道,泛爱群生;而且天还是最终评判者,行使赏善罚恶之职。当然,该生态伦理思想是有世界观前提的,在董仲舒的眼里世界图景是这样的:天为至尊,生养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但人为天下最贵,而且天人相类、天人相通、天人感应,人应当追求和达成“天人合一”的理想。我们来详细谈谈董仲舒的生态伦理观。董仲舒认为,上天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人类是上天管理自然万物的代理人,“人受命于天”(《春秋繁露》中多处这样叙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人受命于天”的,不过董仲舒认为“天”并不是受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天在人类中间挑选了一个代理人——天子 (即皇帝、王者),唯有天子才是直接受命于天的,其他人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又,《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再又,《春秋繁露·立元神》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由此可见,上天真正委托管理天下苍生的代言人是天子;天子是直接受命于天的,其他人是通过天子而间接受命于天的,通过天子之手来管理人类,再通过人类来管理自然万物。这种层层递进关系,《春秋繁露·顺命》作了详细的论述:“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既然人是受命于天的,那么人的道德、行为等就必须要符合上天所规定的准则,即人类行事必须要“法天道”,“顺天命”。《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那么天道、天命是怎么样的呢?《汉书·董仲舒传》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也”。天道是“任德不任刑”,主生不主杀,仁爱天下众生,所以作为天的代言人——王者,就必须法天道,也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制定的政策法规以仁爱天下众生为主。“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又,《汉书·董仲舒传》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上天“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即无私地养育万物;而作为人君的“圣人”也要效法天道,做到“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广施仁德,无私心地爱护天下众生。《春秋繁露·离合根》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又,《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可见,“仁”是天道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人主的天子,必须要法天而行仁道。《春秋繁露·离合根》说“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又,《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因为“仁”本身就是天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君王要法天道,就必须要讲仁义,推行仁政。而“仁”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首先就将“仁”作为核心内容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孔子的“仁”主要是爱人类。《伦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的亚圣孟子将“仁”的内涵由单独对人类的爱扩展到自然万物,他的著名论述是:“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董仲舒先生的“仁”是对先秦儒家“仁”的内涵的继承和发扬,他的“仁”也是不仅要爱人类,还要爱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即“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篇对仁的内涵作了清晰而著名的说明,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可见,董仲舒的“仁”的内涵是明确包括爱人类,以及爱代指天下万物的“鸟兽昆虫”的。
董仲舒描述的理想社会蓝图除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人们安居乐业之外,还有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春秋繁露·王道》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理想的太平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即“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又,《汉书·董仲舒传》说“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由此可见,自然界各种生物的繁荣昌盛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美好是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是君王的责任之一。总之,上天受命于天子,就是让天子把天下管理好,天子应当行仁政,泛爱群生,要让百姓安居乐业,要让天下的群生繁荣昌盛,要让生态环境和谐美好,使人类与自然万物都繁荣昌盛。
天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最终评判者角色,行使赏善罚恶之职。上天的赏善罚恶是面对天下苍生的,但是,最主要的约束对象还是作为上天代言人的人类最高统治者——天子。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君王的统治之下,对他的约束,也就是对人类的约束。董仲舒认为,对于有道的君王,上天是予以奖赏和鼓励的,表现为没有灾害,风调雨顺,天降祥瑞到人间。《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说:“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又,《春秋繁露·郊语》说“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而对于无道的君王,上天是先降灾害予以警告,如果不知反省悔改,则出灾异予以威慑,如果还是不知反省悔改,则灭之,并重新选择代言人。《汉书·董仲舒传》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又,《春秋繁露·必仁且知》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上天会对君王进行惩罚,归纳起来可以说是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过失,一是不能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安定团结,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表现在君臣失和、骄奢淫逸、搜刮老百姓、暴虐好杀等,使天下民不聊生;二是破坏了自然环境,使天下群生遭殃、生态环境失衡等。《春秋繁露·五行五事》说:“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我们再来看看桀纣灭亡时的极度奢侈淫逸、人神共愤的暴政,对人民的摧残和对自然万物的破坏,“桀纣皆圣王之后,骄溢妄行。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饬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尽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饰,穷白黑之变。深刑妄杀以陵下,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灵虎兕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赏佞赐谗。以糟为邱,以酒为池。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诛求无已,天下空虚,群臣畏恐,莫敢尽忠,纣愈自贤。周发兵,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共诛纣,大亡天下”(《春秋繁露·王道》)。“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饬材之工……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尽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饰,穷白黑之变。……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灵虎兕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赏佞赐谗。以糟为邱,以酒为池”,这是过分的奢侈淫逸。“深刑妄杀以陵下……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这是让人人神共愤的暴政,是对天下民众的摧残。“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这是对自然界生灵的摧残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正因为桀纣使天下百姓遭殃,使自然万物涂炭,所以上天便叫他灭亡,“大亡天下”。
总而言之,如果君王效法天道行仁政,泛爱群生,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还能使禽兽草木等自然万物欣欣向荣、繁荣昌盛,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境界,上天就会降祥瑞到人间,出现“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天为之下甘露”(《春秋繁露·王道》)的美好景象。否则,如果君王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天下生灵涂炭,虫鱼鸟兽、花草树木等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上天就会“上变天,贼气并见”(《春秋繁露·王道》)予以警告,如果君王还不知悔改,上天就会让其“大亡天下”,改朝换代。
董仲舒在他的学说里把天建构为最高的神,天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间的所有事物,天是宇宙间最尊贵的,为百神之君。天在创造万物的过程中,对人类是特别钟爱的,因为人类是上天根据自己的模样创造的,因此人类具有高于万物的品性,是上天安排的用来管理世间万物的代言人,其地位仅次于天和地,为天地万物间最尊贵的,是可与天地参的。天、地、人共同组成万物之本。人类是上天安排的用来管理世间万物的代言人,是受命于天的,因此人类必须遵循天道。这个受命主要是通过人类的最高领导——天子来实现的,天子直接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间接受命于天。天道是仁慈的,生养万物,“任德不任刑”,因此人君必须行仁政,泛爱群生,必须维护和保持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万物的和睦与繁荣。世间的其他万物是上天用来供养人类的,破坏毁灭他们就是在毁灭人类。上天是最高的神,还担当着赏善罚恶的最终审判者角色,如果某位君王不遵守天道,不行仁政,让天下民不聊生,使自然万物和生态环境惨遭毁灭破坏,那么上天就会出灾害警告他;如果不知悔改,就降灾异惊骇他;如果还是不知反省悔改,上天就会灭亡他,然后重新选择天子。
董仲舒的这套理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其主要理论是属于神话色彩的,没有多少科学依据;但是,它在维护人类社会稳定和谐,在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却是有积极作用的。爱人、爱护天地间的所有生灵以及爱护生态环境,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理想道德目标,即“仁者”。而且,在人类的头顶上还有天这个最高的神在注视着人类的行为举动,如果有人敢做出伤天害理,危害众生的事,即使是贵为人君的王者,上天也会叫他灭亡。这就在人们的心里给了一个无形的法规标准,时时刻刻约束、威慑着人们,使人们不敢破坏自然环境,自觉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进化。
关于董仲舒的生态思想,当今有些学者进行了研究。著名学者刘湘溶先生认为,董仲舒的理论,字里行间闪烁出光彩夺目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虽然产生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古代中国社会,但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生态保护,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学者黄孔融认为,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蕴含着跨越时代的合理因素和历史价值,其中表现出来对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尊重,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思考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能从中看到与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相契合的一面;重新认识和研究它们,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有助于弥补现代生态伦理构建中思维方式的不足,可以为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提供理论基础。学者丁东风认为,董仲舒思想所阐发的理论和观点以及其思考问题的方法对理解和解决现实社会生态问题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学者陈豪珣认为,董仲舒从宗教神学的宇宙观高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终极关怀。
董仲舒的生态思想在今天仍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为解决当今的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哲学上提供借鉴和参考。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为现今的社会发展服务。
2.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在宋代的成熟
宋代大儒朱熹在传承孔孟“仁民爱物”即以人为本和谐生态观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朱熹(1130.9.15—1200.3.9)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福建省三明市),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遁翁、逆翁,别号考亭先生、紫阳先生、云谷老人、沧州病叟。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继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南宋中后期、元朝、明朝、清朝四代将近千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被统治者列为官学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朱熹的思想还对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王国等地方起过重大影响,这些地区也曾将朱熹的学术思想列为官方哲学。
朱熹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从人文社会到自然科学,无所不包。就仅是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方面,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鉴于朱熹学说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都对其思想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相关著作和文章多得不胜枚举。
朱子的著作很多,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可分为好几种形态,一是朱子自己的论著,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八朝名臣言行录》等;二是别人整理或编辑的朱子著作,如《朱子语类》;三是朱子对儒家经典或重要文学、文化遗产所作的整理和研究之作,如《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又名《昌黎先生集考异》)等;四是朱子与他人合作的著作,如《近思录》。朱子还整理和编辑过他人的著作,如《二程遗书》《上蔡语录》《韦斋集》等,当然这些严格来讲不是朱熹自己的著作。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或称《渊鉴斋御篡朱子全书》),但实际上是朱子的《文集》和《语类》的选集本。现代,朱杰人先生主编的《朱子全书》(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由海内外学者共同完成,耗时8年,有27册,约1436万字,基本上囊括朱熹的所有著述。
当然有关生物(包括人)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是朱熹博大学问中的一小部分。从总体上看,朱子的生态思想是对先前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朱子有关生物与环境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见到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先前大儒的思想的影子;朱子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观点是,人与自然万物同源,都是“天地”所生,都源于天地之“气”,但人最灵、最贵;天人相类,天人感应,人要辅助天地行管理之职,使自然万物共享繁茂。不过,对于人和自然万物,其伦理地位是不同的,各自享有的伦理关爱有等级差别,对人要“仁”,对物则是“爱”。我们再来仔细看看朱熹的以人为本和谐生态观。
在朱熹看来,人类具有比自然万物更高的伦理地位,这反映了朱子对儒家人本和谐生态观的一贯继承和发扬。自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始,人和人的价值就一直是第一位的,《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儒家亚圣孟子,把如何对待人与物的态度作了总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荀子也认为人是天下最贵,“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大儒董仲舒同样也是认为人类为天下最贵,他说“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朱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先前的儒家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朱子对儒家的生态伦理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和细化的规划发展。朱子对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有如下注解:
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杨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所谓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无伪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上》)
通过上面的注解可以看到,人和物所具有的不同生态伦理地位,对人对物应该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感情,以及人的主体地位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显而易见,清清楚楚。朱熹的这段论述就是我国传统以人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的核心内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以人为本的生态伦理观并不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号召人与自然对立;恰恰相反,儒家的生态伦理观是一以贯之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从儒家的鼻祖孔子开始的。孔子“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董仲舒“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程颢“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二程遗书·卷四》)。可见儒家在树立以人为本观念的同时,对普通的自然万物是主张爱护的,不要去征服和破坏自然。就如程颢所描述的一样,人作为本体,其他万物作为人的四肢百体,整个自然界就是以人为头的一个整体。而对于人类必须要向自然界索取的各类资源,儒家则主张的是一种“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竭力维护“人-自然界”这个有机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贯穿于儒家始终的传统人本和谐生态思想,到朱子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人本和谐生态观,对指导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有价值的,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生态环境日益被严重破坏的今天,发扬儒家人本和谐生态思想对于保护生态环境、阻止浪费破坏资源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儒家尊重人、肯定人,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又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儒家人本和谐生态思想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不一样的,“人类中心”主张征服和掠夺自然界,主张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本和谐生态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整个世界是“人-自然界”这样一个有机整体系统,人只不过是这个生态系统的“头”,而其他自然万物则是人的“四肢百体”。同时,儒家人本和谐生态观与当今西方一些极端激进的生态伦理思想也是不同的,这些极端生态思想主张消减人的价值主体地位,湮灭以人为本的观念,把人的价值地位下降到与自然的动植物相同的位置,很显然这也是行不通的,是不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笔者认为,无论是在今天抑或是在未来,综合考虑过人和自然两方面的儒家和谐生态思想都是行之有效的、先进的、科学的,是能够良好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观之一。因此,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笔宝贵思想财富,我们应当好好地继承和发扬。
摘自《问道自然:中华传统生态智慧》
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