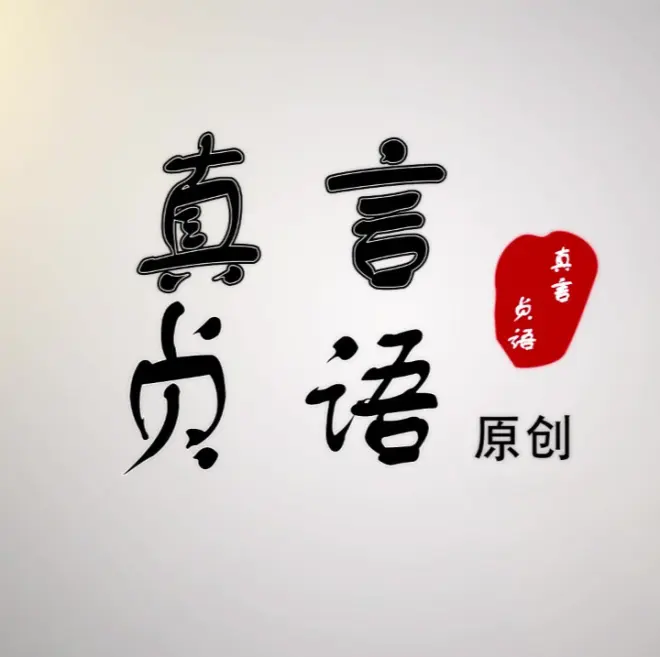张刚散文丨一盏偏头路灯——回乡(之三)

一盏偏头路灯
——回乡(之三)
文/张刚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在沟畔,一盏太阳能路灯,亮起了。
照亮了两户人家。
路是2017年夏天拓宽的,铺了细沙,也筑了水渠,小汽车可以轻轻松松地开到打麦场了。
这是西北高原上一个最为普通的乡村,十多户人家,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坡上,而最低处,只剩两户人。
春节期间,在宗族牌位家谱摆在堂屋中央,家谱记载,这里最早可以上溯到嘉庆8年,祖上从离此地大约40里远的陇上大先生——牛树梅的故里搬来这里,算起来,当属一个牛家。
虽经各种战乱,但一直以耕读传家,繁衍至今。
从沟畔上面的平台遗址推算,这里曾经有五户人家,其中两户已搬到山腰,另一户举家外迁,门长年上锁,老屋已坍塌崩坏。
只剩这两户人家,岳母在城里看小孙子,妻嫂也去城里照看小孙子,家里只剩下了岳父和妻哥,另一家也是远亲,孩子进城务工,当妈的就跟着去看小孙子,当起了不领钱的保姆。
于是这两处庄院,大年过后,就只剩三口人了。
人少了,日子显得更加漫长,太阳在空中挪得太慢了,岳父搬个小板凳坐在沟畔,对面的高山,一天只有一趟乡村公交,每天凌晨六点,从山沟底爬到镇上,再从镇上翻山越岭到县城。下午两点半从县城返乡,慢慢悠悠再次翻山越岭,在下午五点左右回到乡下,再从山道上拐来转去,回到山村。
一年,能够盼来的,只有过年时孩子从外地回来,为庄院里增添些许热闹。
对家乡的长夜来说,这盏路灯太亮了,从晚一直亮到早。关键是,安装时照顾了打麦场那边的路,那边的光多,院子这边的光就少了,安偏了。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生态自然就有了改善。像山沟,本来有路,但没有人走了,就没有了路,于是长满了各种荆棘,野草。荆棘野树林中到处是锦雉,关关叫着,飞起来时拖着长长的五彩长尾,煞是漂亮,这是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允许猎杀。家里的小狗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处,有时会跑到沟底把它们一只只赶起来,飞向远方去了。
锦鸡看着漂亮,可让农民叫苦不迭,玉米种子被它们从地里刨出来吃掉,还得再去补种,农民伯伯在地边扎上稻草人,挂着衣服,可吓不住这些聪明的家伙,它们很快就知道这是假的,甚至飞到了稻草人的头顶上。
这盏偏头路灯,本来是照着打麦场多一些,门前小道的光就少一些,需要转转头。过完年了,等孩子们都离家了,就把它的头转向院子里来。关键是,即使这两户人家,过完年有一家也要搬到后山上的新庄院了。
恐怕到那时,就只剩一户人,一个人。再过几年,如果也迁走,这处小村落就再也没人了。
这盏路灯,能否依旧守护?

【作者简介】张刚(男),甘肃通渭鸡川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山东齐鲁晚报高级记者,现供职于山东管理学院。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曾当选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十大杰出青年,2017年当选为十九大党代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著有《底层行走》《乡书何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