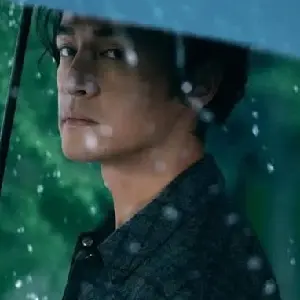那些爱上文学的年轻人
本文共计1803字,预计阅读5分钟。
你好哇,我是林小西。
昨天晚上逆熵增合伙人群里聊起线下见面会。
讨论会去哪座城市?
勾起了我的旅游回忆。
于是我打开QQ相册,翻看之前去过的地方,往事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
原来,之前去看了那么多祖国的大好河山;
原来,文艺主义情怀从非常久远的时刻就镌刻在我的骨子里了。
现在回头看,虽然感觉有些矫情,哈哈哈……
但是,那大概就是逝去的青春吧……

01.
想起之前在厦门工作时,有一次去十点书店。
在木制书柜的一侧,赫然写着佩索阿的一句话:
文学是忽略生活最为愉快的方式。
许知远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小职员”一篇中,对诸如佩索阿、博尔赫斯、卡夫卡此类小职员做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介绍。
在白天,他们披着小职员的面纱,面无表情地行走在人群之中,观察着别人;
夜晚,他们撕下那层暗淡,在夜色的隐藏中,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准备篡改或制造历史。
费尔南多·佩索阿生活在里斯本的一条叫作道拉多雷斯的街道上,是一位助理会计师。
他的住所也在同一条街道上,那是一个供他写作与幻想的地方。
他的全部空间就在这里,他的生活与艺术就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展开了。
这位被称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的小职员,在《惶然录》一书的序言里,自我嘲讽道:
因为他没什么地方可去,没什么事情可干,没什么朋友可拜访,也没什么有趣的书可读,
所以每天晚饭以后,他总是到那间租来的房间,用写作打发漫漫长夜。
博尔赫斯,尽管在他的后半生,他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但是他似乎还是喜欢孤独一人走在阿根廷的街头,或者静静地坐在玻璃窗后发呆。
而卡夫卡,则在布拉格一所意外事故保险所当办事员。
他坚持“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认为以写作为职业是可耻的,所以他需要一份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
他们都是普通的小职员,生存在狭窄逼仄的空间里,却在文学中,找到了安顿自己灵魂的一席之地。

02.
我的偶像王小波,一个有趣的人。
他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
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在文学上有一定的建树。
但他其实还是一个程序员,并且是一个很牛的程序员。
算起来,王小波是我国的第一代码农。
在国外留学期间,就给导师做高级打工仔——写程序。
之后研究Windows系统,学习汇编和C语言,通过卖软件挣了一些钱。
当时很多中关村的老板想要拉他入伙,但是被他拒绝了。
因为内心里还是喜欢写小说。
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写小说,便是王小波安顿自己灵魂的充满诗意的世界。
同样受到王小波影响的,宋小君,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
他曾经写过一段话,我后来经常会引用:
写作是一个关照自我的方式,将所有的“郁结于内”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发乎于外”,内心有了悲悯,精神才不至于抑郁。
文学,便是与自我、与生活达成和解的方式。
阅读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得以窥见那些年代久远的人物。
让我们超越自身的经验局限,从更高的维度,去洞见生活的真实。

03.
写作,便是自我的救赎。
曾获“鲤·匿名作家计划”首奖的小说家郑执,在新书的后记里写道:
人渺小又无谓的一生中,神不可能时刻在场,我选择用写作弥补它的缺席。
拿起笔,我是我自己的神,我给我自己指一条生路,
放下笔,我仍是尘埃,是野草,是炮灰,是所有微不足道的子集,于现实中坦然地随波逐流,从不迟疑。
日常生活中,我们逃不出“千人一面”的琐碎:
每天早起、通勤,穿差不多的外衣,进差不多的写字楼,做着差不多的工作。
夜幕降临,带着些许倦意,通勤,归家。
日复一日,人与人的生活何其相似!
然而一旦踏入文学,我们便不再是面目模糊的“大多数”:
那些内心难以为外人道的骚动,那些无处寄托的妄想,那些独属于你,看似古怪的迷恋与狂喜,
都能在文学这无所不包的流域中,精准寻获与自己心灵匹配的那条支流。
于是神迹在这一刻显现,我们与它灵魂相认,被它纳入怀中。
文学,让我们得以摆脱生活表面的相似,成为自己精神世界至高无上的王。
04.
这也就是为什么,热爱文学的人,对人与事,对世间欢愉和磨难,总怀有深刻的悲悯。
在文学中,我们不再只拥有此刻的生活,也不再只困囿于自身贫瘠的经历、情感——
文学,让我们有处可逃,更让我们有梦可做。
参考:
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三联生活周刊《梦幻联动!只为热爱文学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