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冈村宁次回忆录》看日本投降:为何他们不承认失败
全篇声明:笔者仅从史料等角度分析或阐释当时的情况,不偏倚军国主义,更不危害国家安全,辱没国家声誉。请各位读者审慎阅读。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9月2日,盟军同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订停战协议,宣告日本在各个战区的正式投降。自此之后,日军所分布的东南亚、太平洋、缅甸,越南、朝鲜、中国(包括台湾及伪满洲国地区)等各个区域逐渐被解除武装,战俘、武器等各类战败国资源也或分配或销毁等处理。然而在当时,各个国家的处理方式并不相同,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态度相当友好,而日军却趾高气昂,虽然得到了中方的尊重和帮助,战后的表现却令人心塞。本系列各篇着重讨论的内容即日本在中国投降中,中方和日方的诸多情况。

和平投降:日军为何顽固地不承认他们的失败?
笔者注:本篇主要是观点的一个总览,还会陆续写更为详细的文章。
在当时的中国整体区域内,分别原属于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沦陷区的关内和关外几乎是两重天地。当时的关外乃至长城以北的不少区域都是在苏军远东方面的控制之下,就苏军对日本战俘的处理态度,这似乎是几十年以来东北地区日俄争端的一种延续,当然,这不是本篇或本节的主题。
关内,即中国大陆剩下的部分和台湾等地,在投降后却是另一副光景:日军驻军没有进入战俘营,没有立即投降,各层级的指挥系统仍然在运作,乃至于驻军不撤离,组织不停摆,就地更名,所谓等待接收期间也偶能见到暴行。这种情况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在西方盟军控制区域的样子,倒像是日本在割让占领区一般,可这又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日军,除了真正意义上在前线野战的部队,尤其是遭受痛打的湘西前线、桂柳的一些部队,大部分居然仍然自以为胜利在望,理应努力。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战略反攻计划主要就集中在桂柳一带,而该处日军又是中国派遣军仅有的几支野战编制部队,“旭”集团(第十一军)和“波”集团(第二十三军)在1944-1945年间虽然实现了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大胜,却也见识到了诸多恐怖,如衡阳战役和桂柳的一系列战役(衡阳战役日军的伤亡根据战后文件披露已达到数万,这场战役对日本国内的震动极其大,以至于战果公开都是问题),总之虽然从战略部署上似乎没有折损长官们的欲望,士兵却也多有所不耐。而在其他方向上的各个总军,出于分散驻守或无大作战行动的情况,底层士兵的意见有限,在上海、南京地区的驻军则根本未见问题。当时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记述道:“前线的少壮军官及一部分下士官或愤慨,或哭泣,或胁迫部队长强烈要求继续作战等情况不断发生,各部队长为说服他们,费了几天的功夫。军官及下士官悲愤之余有自杀者。各部队对自杀者都倒填日期按战死处理,因此人数不明。但当时据我所知,仅长江下游地区,即有某大队长(少佐)以下二十余人自杀。”
少壮派军官能够出现在里面,毋庸置疑是因为宣传,当时日军野战部队普遍其实缺乏下级军官以及预备役补充的军官。这在1944-1945年等作战中均有体现,如衡阳战役期间,参战的伤亡最重的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一一六师团几乎全都是指挥官死伤殆尽,往往火线提拔,中队长充任大队长,甚至连充任的中队长也属于火线提拔的不在少数。在豫湘桂作战后期,则往往能见到日军以下级军官、预备役甚至上等兵充任中队长的情况,且推进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传统军校教育,有良好修养的日军老派的基层军官大量流失,而大批接受狂热军国主义洗脑的少壮派军官在很多区域内维持着下级的局面,导致其即使吃了几个败仗,也坚信胜利在望,而那些因稀释部队编成的师团,同样因为少壮派军官的比例,几乎不可能认为他们能对投降采取积极的态度(像这些自杀的军官和士兵,最高级别为大队长,而这一职务往往已经可以由新锐军官充任)。这也正是军国主义的狂热,或者说是日本数十年的民族教育造成的狂热。
实质上,在1945年投降之时,日军前锋的野战精锐大多已经是强弩之末,这些前线的部队受到的除了中美空军三班倒的定点打击,还有重新武装和组织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民团民众的袭扰、游击队的偷袭与拔点或有组织的进攻。这些前线区域毋庸置疑很快就会接受投降,而且他们经历了后期的近乎毁灭性的作战之后,也难以再趾高气昂,少壮派军官的存在是一种严重的阻力。

但是,在日军牢固控制的一些区域,尤其是各大城市、中小城市等的警备队,局面则完全不相同。抗战胜利前的几个月,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以很快的速度光复了不少中小城市(国民党方面的敌后反攻也一样有所战果,但相较于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等部的迅速作战,战果差距是尤其大的)。然而很多日军驻守的据点要么出于时间关系,要么出于距离关系,没有能力及时收复。在这些区域,日军的警备队或驻守的原属常备师团下辖的(有些部队的确是由野战师团缩编时转隶出去的),甚至后方作战地域具有野战能力的部队,仍然可以伙同伪军形成继续的控制。不仅没有尝到什么大失败,也难说会认识到大势已去的感觉。
应当说,日军在后方驻防地域的猖狂,个人认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伪控制区的反攻不足以让日军认为自己趋于战败。以华东为例,著名的车桥战役等大多是针对以伪军为主,日军为辅的作战,纯粹日军从建制上遭到威胁的打击屈指可数,一次性的大战果寥寥。零敲碎打会给日军造成大量的累计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统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仅仅对日军造成的损失确实极其可观,因为灵活的战术,虽然日军态度和对付其他游击队一样,但往往伏击方承担更小的损失),但是在日军部队的角度上则往往难以明晓自己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一直到抗战前夕都在持续的扫荡和巡逻,除了偶尔的灰头土脸,对指挥机关几乎不存在致命打击。而日本投降后,这些守备队也就继续着守备任务,虽然没有太多明目张胆的屠杀和扫荡,但由于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几乎完全无权接管这些区域,日军的实际控制使得半高压仍然存在,居民除了放放鞭炮往往根本不敢和日军硬碰硬。也就是说,在等待投降的期间,日军几乎完全处于之前的地位,本质地位没有变化,除了知道自己应该投降以外,都像是当时冈村宁次的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一样:皇军及侨民应坚持不屈气魄及斗志。悲哀的是,这些“皇军”的不辱名声却是中国的灾难。
要知道,当时的日军在被接收前仍然全副武装,行“警备”之实,主动权仍然在日军手中,即使在投降之后,日军在上船离开中国前还能继续保留一定比例的武器。在等待转移的过程中,虽然可以看到暴行的显著减少,但暴力事件还是会时有发生。在日军口中,这就是所谓“治安”,因为国民政府没有给地方任何直接权利去自发接管,沦陷区在日本投降后仍然能存在。
这也可谓是当时投降中出现的一种弊病,笔者会在之后的篇目中进行讨论。

因而,在当时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总能看到些许现象:由于国民政府部队很快就会进驻,从日侨到日军都竭力自保,转移资产和掠夺来的资源。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记载许多,摘抄一例如下:“据上海财界元老亲日的周善培向他的一个日本友人透露:刚一停战,日本中、小公司的社长们陆续来访,纷纷提出想把他们会社的名字改在我的名下,继续营业,平分利润等,我一律拒绝了。我多年标榜亲日,但很少象今天这样瞧不起日本人。”
相对的,在当时的乡村和中小城市,所看到却是居民或许可以欢庆抗战胜利,而日军仍然能荷枪实弹地继续巡逻,只是稍微“收敛”。在太原,甚至有称日军还能在街上放狗咬人的这种可怕情况。即使在伪军独立驻守的城市,如果指挥官有点“匪气”,那居民的命运亦会不亚于军阀时期的惨状。
总的来说,当时的日军在投降之时,在很多区域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承认战败的样子。至于原因,也可大体如此概括:
1. 对地方游击队的扫荡等作战,接受零敲碎打的损失,但少有指挥机关和部队组织的彻底崩溃,主动权依旧存在,使得他们自认为不能明显地感到劣势。
2. 前线的野战部队,直接明晰了目前情况,对战败事实也可供认不讳,但由于少壮派军官等的存在,也一样会严重抵制,乃至爆发自杀等恶性事件。
3. 各地驻军或留守部队,出于投降条款和接收部队的长期不抵达,仍然全副武装能行警备,致使原沦陷区投降意志淡薄。
4. 这一点文章中没有写,但是在投降和转接的这一点上相较各国,中国的所作所为可谓仁至义尽,但也给了日军太多得寸进尺的空间,对于这一矛盾,我在下一篇会有所谈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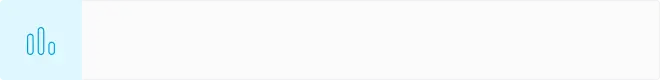
参考资料来源: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1981版 中华书局
关河五十州《一寸河山一寸血》
网络关于部分战役的资料(知乎为主体),出处比较冗杂不一一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