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哪写到哪——无法表达的狂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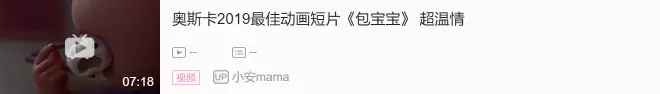
无论是《包宝宝》还是《青春变形记》都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没有表达对电影的期盼,而是提出了更多文化层面的批评,但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需求,即“我想要看到我自己”,而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今极度需要被满足的需求,也是为什么部分电影即便内容一般也能获得极高票房的原因之一。
到目前位置,在新时代的文化策略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一直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外国电影的大行其道,电影院中充斥着好莱坞面孔,他们用极高水准的技术统治着观众的视听体验,满足着隐性的激情需要,当然这一点在近些年逐渐改善。其二,电影院的国产电影缺乏具备总体性的形象代表,这一点就不得不联系前一点,好莱坞的统治业已走向终结,但国产电影的面貌依然模糊,当然已经有了一些代表作品,但想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大众化风格体系,还需要很多很多。
在这里就出现了那个问题,到底我是谁?黑暗的影院中闪烁的银幕照亮着每一个观众的面容,然而这道光又将把人带向何处呢?通过大众媒介大肆传播的电影并非无辜的,它如同不会反射的镜子,将面容加于观众,这一点在涉及历史题材时最为显著,它高声说着我们是这样的,观众自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这算盘归根结底也并非自带的,而是过去获得的。过去的小算盘使我们能够抗拒也能够认同,但在今天又显得不够明确,有许多不同的答案。

回到《包宝宝》和《青春变形记》,总结来说对它们的攻击来自于其中的中国元素,在异乡的中国元素其形式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回忆,因而它们构成了与我们相对的镜子中的形象,但这说到底是误认,它是北美华裔的,而不是中国大陆的,而后者的镜子依然被水雾所遮蔽,身份证还在寻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