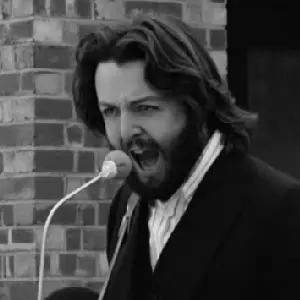性的概念
当我们谈及生产,就必然的需要回顾劳动力在其中的积极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再生产——斯密与其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当中所阐释的乐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运动过程的抽象演绎。而抽象演绎的未来蓝图成为现在的此时此刻,无产阶级有权就自己的生存问题对抽象推理进行考验:当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称呼这为之其作为其社会职责时,无产者也当就目前的社会矛盾进行反击,就此将注意力的焦点当下化。那么,那些什么所谓关乎思维习惯的问题,也必定变成权力问题。 但是这不是我这次探讨的兴趣所在,接下来,我将继续进行我对于性的阐述,之后在进行总结。 性的再生产(我已经提及了关于再生产的范畴中,其对于现实活动的普遍性了),其实质来源于人对未知的试探,因为已知的性一直在成为情色本身。而情色是性活动规律性的再生产的表述词。反之,信其自身在“进行时” 时,是一种反思力驱动的再生产。在这个层面上,未知、不在场的体验也恰恰是有反思所驱动的。 所以,这应当被划分为两个相互区别的意向性位面:其一是完璧归赵的完成时,我将其统称为情色活动。这是无意识层面所促成的。其二是仍然处于进行时,由反思力所驱动的尚未被命名的不确定状态。而这是由意识层面所促成的。 就此,性成为了强迫性重复在意识层面无法被超越的“尝试”,在这层面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就可以理解弗洛伊德的“太一”——性欲本位的阐释:一种悲观主义的后撤(回溯)。即,人是由性欲的无意识所驱动的。 而回到开头问题,显而易见难道不是:处在再生产条件内的劳动力们,处于被完成规划了的生产秩序内部;而能够进行再生产规划的,不恰恰正是那些可以就生活现状进行抽象演绎的资产阶级吗?如果我们是介于普罗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权力利刃的白手套;如果我们介于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这就仅仅是观念问题。 就在这个阶段,有另一个解放意味的关键:人在意识过程之中,对于自身的欲望,需求甚至是伦理热忱之外的价值意象,还存在着一个无法不被接受的对象。 就此问题所关乎的“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我存在”的基本本体论问题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切的哲学命题,其对象就其无法继续进行抽象思考思考,本身而言就是在一切充盈的纯有(所有的匮乏,在将要变成欲望之前,就已经以可以不必改变就能够再生产的现状之名的需要被取消了)之外的剩余。就此,我们可以领略拉康的主体性:“因为我欲望,所以我存在”,主体得以立刻被当下化,也就是那时间一时之中自身位置的确立。 那么这也即我所理解的辩证法运动: 因为“非欲求”的欲求作为符号秩序,永远无法中介于意义的质料(欲望的本真性)。 拉康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变革性在于:主体性的纬度以一种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实在界:Include me out)回归,成为了不必以“太一”之名中介的“自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