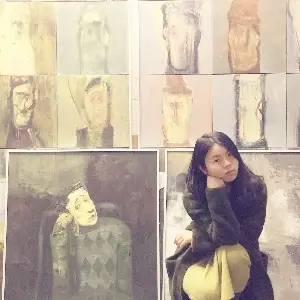中医药 | 一把退休的老刨刀

文摘:
夕阳斜照,二姨古铜色的皮肤平滑匀亮。我记得一个多月前,她从枕头下摸出老刨刀那次,她的皮肤被刨刀上的锯齿刮的血肉模糊。如今,一道血杠子也寻不见了。
和别的老太太爱在枕头下藏存折、藏照片、藏药片不同,二姨的枕头下常年压着一把钢制的老刨刀。这种习惯,已经保持二三十年了。
但,并不作防身用。
刨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流行的款式,现如今已很难得见。
我也是月初从城里搬回乡下,和二姨同住,睡前再次看见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闪着白光的钢制品,才记起这物件儿的功能和模样。

压在枕头下的老刨刀
刨刀长约二十厘米,宽约两到三厘米,形状有点像茶道六君子里的茶则,一整张钢皮敲制而成,合四种刮皮功能为一体。
以抓刨刀的手柄处为分界点,上下各分布两种刮皮功能。手柄下方的圆筒部位上有一道半指长的裂口,这裂口把钢片从中间分为上下错综半毫米的两片,凸起的这一片充作刀刃,用来削瓜果皮;尾部有一个半圆形的刀片,像拇指甲盖儿,用来挖瓜果的腐烂处。手柄的上方,是一块左右两侧朝下弯折的方形钢皮,钢皮的背部打有两排鱼鳞大小的圆孔,圆孔内一半材料舍去,一半保留住,敲成往上凸起的十几个小刀片,用来擦土豆丝儿,萝卜丝儿;弯折下去的边沿各有一行锯齿,用来刮鱼鳞。不过,小时候,家家条件都不宽裕,鱼是不到大年三十吃不到的,这专门为刮鱼鳞设计的锯齿功能,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一闲置就是一整个年头。二姨却天天用它来刨奇痒难耐的皮肤。
打小我就记得,二姨每晚睡前都会把四肢的皮肤刨一遍,起先是用指甲,之后改为梳子,当梳子的齿尖也不能抑制这种奇痒之后,她把厨房的刮皮刨子拿来做最后的抓痒工具。一抓就是几十年。
二姨的皮肤病从我开始有记忆起,就自生成了,说不清是怎么得的,看过不少医生,根本拿不到根儿。我们姐妹以前在外地上学,也向人打听,买过各种膏药带回来给她涂抹,一点用处也没有。记忆最深刻的是曾被推销员在各个列次的火车上卖力吹嘘的万能老虎膏,说这种来自越南的珍稀洋货是所有痒病的克星,我光看包装盒上画的那只龇牙咧嘴的白虎,也觉得它的药效威望至极,带回来一盒给二姨涂抹,结果也是无用的。
我没有想到这种只能伤及表皮的痒病,连名字都叫不出,却这样顽固,可以从一个人年轻跟到年老时。
二姨摊开手掌,把那把老刨刀展示给我看,笑着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东西算不算老古董了?当真是我陪伴了我大半生了!”
我接过刨刀,细细打量,顿觉惊恐,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像划过脑海,五味杂陈。刨刀呈黑白分明的两种色泽,那十几个鱼鳞般的小圆孔,因为功能用不到,也容易积灰,难以清理,结着一层厚厚的黑色包浆。那手柄部位,又被手心儿的皮肤磨得闪闪发亮。锯齿部位也是程亮的,齿尖儿的刃虽然已经被磨平,每一道转折处的闪光似乎依然能割瞎人的眼睛。

二姨的老刨刀
这种样式的刨刀,早就淘汰了,一个村子怕是也只能找出这一把来,跟五花八门的新款式刨刀比起来,它在削皮功能上确实不占优势。
“你现在还在用这个刮皮肤?”我问二姨。我中间将近有十几年不在家乡,对二姨的生活习惯已不明晰。
“是啊,每晚睡前不用这个刨一遍就睡不着呗。”
说完,二姨搂起她的裤腿,面带笑意的将这个陪伴了她大半生的老古董的锯齿尖再次对准小腿上的皮肤,来回刮弄。她娴熟又轻松的样子,好像不是在刮自己的皮肤,而是在刮一根没有疼痛知觉的干树枝。
她身上被抓坏的皮肤,确实像杨树皮一样粗糙,泛白,分色不均。
我蹙着眉,咬紧牙关问二姨:“这样刮,不疼吗?”
二姨边刮边笑着说:“哈哈哈,不刮又痒,刮了又疼。没得法!”
“那上次刘医生给你治胃病,号脉时怎么没把这个症状也说给他听?”
“当时没痒,我没想起来。过后再去麻烦人家,我又有点儿不好意思。”
刘医生是二姨的儿媳妇给我介绍的对象,一名在中医领域精进十多年的年轻中医,我们在疫情道路解封之后第一次见面,算下来,已经相处两个多月了。
他长得虎头虎脑,说话行事也虎里虎气,记得第一次见面,我就被他的大嗓门给吓得打了一个惊颤。像我这样心思细腻的人,很难想象日后要和一个大老粗长久共处一室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极不协调。
慢慢相处之后,我发现他虽然外表粗犷,但心思极为细腻,尤其是在对待病人的时候,他有超强的耐心。在一个乡镇医院工作,他面对的病人多是留守在家乡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耳朵不好使,同一个问题,重复问好几遍,刘医生总是不厌其烦的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大声解释。久而久之,他自己也养成了大嗓门说话的习惯。

刘医生正在为病人针灸
我问他:“学中医吃了不少苦吧?”
他别过脸去,摆手叫我不要继续这个话题:“你问这个,我有点想哭。以前确实吃过苦,但没有人问过。”
国学五术,医有其名。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是华夏文明五千多年的文化积累, 它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时常旁观刘医生诊病,眼见一碗药汤,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帮助病人解除痛苦,心生惊叹和敬畏。我和病人总是情不自禁的发出同样的感叹:“怎么会这么神奇?”
二姨身上的痼疾,就是刘医生的汤药治好的。
年初,二姨经常泪流满面的跟我说她魄不附体,命不久矣。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胃像被钻子钻着疼,浑身气软无力。我半夜听见挖田的声音,她说那可能是她的魂;一只飞蛾扑在我窗帘上,她也说那是她的魂。吃了几个月的西药不见疗效。我与刘医生相识后,他根据二姨的症状抓了两幅中药,服过之后,果然奇迹般的好了,一顿不但能吃上两大碗白米饭,觉也睡得好,田地里的活儿干得也有劲儿,心情也好了,打一个哈哈,几个山头都听得见。她说:“哈哈哈哈,真是个神医啊!”
“刘神医”这个称号从城里传到我们这个小山村之后,乡亲们都来找刘医生看病。我们平均一周一两次的约会,也几乎都会拿来做义诊。仅仅只是依靠把脉,就能把病症说出来,再加上他的银针和汤药,确实能治本,人们对中医药,也有了新的认识。

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正是因为它的神秘,中医行业更容易鱼龙混杂。“伪中医”们并没有理解和掌握中医,但却在使用中药治病,他们就对着中医书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的开几味中药,连最基本的“寒、热、虚、实、表、里、阴、阳”都不会分辩,结果有可能让病人体内的湿寒更寒、热毒更热,不但不能治好病,有时候还会让症状加重。病人不管这个药有没有按照中医理论配成,只要吃的是中药,他们都会理所当然的以为是在接受中医治疗,而“治不好病”的罪名也同样会怪在中医药头上,久而久之,“十个中医九个骗”、“中医不能治病”的偏见理论逐渐占据医药市场。尤其是今年的疫情,中医药在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被打压几十年的中医药名声重振,一大批“伪中医”又横空出世,他们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看了几本中医书,连最基本的“望、闻、问、切”都不会,就敢拿中药治病,不问后果。实在叫人唏嘘!
中医的求学之路艰苦漫长,业内有“师承五年”,“师承三年”的规矩。我同刘医生的师父师娘们共进过一次晚餐,虽然是坐在装饰味儿现代的餐厅里,却感受到了历史电影里才会看到的传统“师徒如父子”的情义,他们不光教医术,也教他为人处事,更关心他的生活点滴,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示子精神。
明师出高徒。过后,我再把二姨痒病的症状说给刘医生听,他又给二姨开了三副敷泡的草药,才用了一副,二姨说不痒了,已经连续一个月睡前都不用老刨刀刮皮肤了。还像上次一样,她依然中气十足的对着山谷打哈哈说:“果真是个神医啊!”
我不信刘神医真的有那么神,一副汤药就能治好困扰了二姨几十年的痼疾。不想,二姨穿着崭新的白衬衫自己跑过来了,她卷起袖口和裤腿对我说:“你看,当真好了,再没抓过了,以前抓坏的皮肤也已经恢复了。”

二姨痊愈的皮肤病
夕阳斜照,二姨古铜色的皮肤平滑匀亮。我记得一个多月前,她从枕头下摸出老刨刀那次,她的皮肤被刨刀上的锯齿刮的血肉模糊。如今,一道血杠子也寻不见了。
我还注意到二姨今天穿的白衬衫很好看,手工缝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款式,米白色的棉麻料子上点缀着蓝色小圆点,素雅精致。我发现她最近一段时间穿的都是清一色的白衬衫,纯白的,绿树叶点缀的,红色波点的,蓝色碎花的......怪不得我觉得二姨最近看起来好像变年轻了。
“你穿白衬衫真是好看!”我情不自禁的对二姨展开赞叹。
二姨又开始笑得只打哈哈,她一边整理袖口一边说,她这样的白衬衫,存了有一箱子,年轻时找老裁缝做的,姐妹送的,女儿买的......以前皮肤痒,总是一刨就流血,怕把白衬衫染上血渍洗不掉,不敢穿。现在皮肤病治好了,不怕染了,她从箱底找出来,一天换一件儿,天天穿。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二姨的新楼房盖好之后,为了表达自己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她在每个房间都睡上一晚上。
一个女人,无论什么样的年纪,能穿上自己喜爱的衣服,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吧!而二姨因为病痛,要把这份喜爱在箱底儿压上几十年,直到古稀之年,才得以释放,我觉得感慨万千。

穿着白衬衫快乐的二姨
又记起跟刘医生初识时,我问他为何选择从医。
“小时候奶奶生病了,我去接医生来家里看病,去了医生家里三次,他都在外面出诊,我才发现我们那医生太少了,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根本救不过来这么多穷苦的百姓,我就决定自己当医生,然后我就去学医了。”
“当上了医生之后的感觉呢?”
“记得小时候,医生在我们心目中是受人敬仰的。都说医生这个职业有多崇高,真正做了医生之后才发现,其实病人才是大爷,他们因为自身病痛,将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导向给你,对你大吼大叫,脾气不好的家属还可能对你动手动脚。你被日觉(本土方言,骂人的意思)的像个孙子,不但得笑脸接着,还得理解和安抚他们。”
“那你为什么还要当医生?”
“因为喜欢啊!”
“当医生这么辛苦,没有周末,还要三天轮一次夜班,通宵出诊。工资不高,却要时刻担当生命风险,你喜欢它什么呢?”
“成就感啊!你想想,当你把一个病人治好了,她乐呵呵的从家里捧两个红薯或者一把青菜叶过来跟你说,医生啊,我没有什么好东西感谢你的,这是我自己菜园里种的,你一定要收下啊!你不收,人家硬塞给你的那种成就感啊。倒不是说贪图那两个红薯,就是你让人家不痛了,让人家从愁眉不展变得眉开眼笑,你也感到很快乐。”
想必,我若把二姨那把老刨刀终于退休的故事说给刘医生听,他一定也很快乐吧!他的大嗓门,打起哈哈来,也能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头,和康复了的二姨一比高下吧!
——杜雯(西窗),2020年6月5日,于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