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戏中的真与假:是狸猫换太子还是审理假皇子

载自《包拯千年之谜》作者春江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从元杂剧《抱妆盒》到清代的小说《三侠五义》,再到当代银幕上的包公故事,其情节始终都没有停止过演变的过程。

跨越历史长河,1000年前所发生的3件事都与这个动人的故事有关。后来的创作者将这3件事的某些部分分别提炼出来,然后加以糅合,历经千年,虽经多次文字的修饰,却依然掩盖不住故事里的真实。
第一件事是假皇子案。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
四月,京城发生了一起冷青案件。
冷青是一个医家子弟,长大成人后在庐山一带漂泊,到处流浪。由于自己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宫女,他就经常在众人面前招摇撞骗,说自己的母亲在皇帝面前得过宠,妊娠之后,被放出宫廷,自己是当今皇帝的儿子。

当时,庐山有一个和尚叫金大道,认为冷青可以利用,就把他挟带到京城,声称一定要在官阙之下叩见皇帝。金大道和冷青两人,在京城之中妖言惑众,胡作非为。一时间,京城之内议论纷纷,冷青也闹得越来越大胆了。

后来,开封府侦得此事,府尹钱明逸就派衙役缉拿冷青审问。金大道看到情况不妙,立生一计,唆使冷青装疯卖傻,顿时变成了一个颠三倒四、神经错乱的狂人。

这日,钱明逸开庭大审,吩咐左右带冷青上堂。

谁知冷青一进堂,就摆出一副皇子的架势,对钱明逸大声喝叱:“明逸,你安得不起!”钱明逸一听,当即怔住,在这真假难辨之际,在众目睽睽的府衙大堂之上,不自觉地站立起来,然后就坐。狡猾的冷青一开始无疑就夺取了主动,而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骗子的江湖之术!

钱明逸亦不是无能之辈,经过盘查审问,根据冷青言语失常、疯疯颠颠的表现,断定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狂人,当然不是皇子。然而,这恰恰又中了金大道和尚与冷青的诡计,使他们逃脱了重罚。

按照宋朝法律,既然冷青只是一个疯子,那就不再是政治骗子,所以钱明逸只把疯子冷青判送汝州(今河南临汝)编管。

此案判决后,有些官员认为过于草率,案件还留有疑点,便反映到仁宗面前。百官上朝时,仁宗皇帝就此案征询大臣的意见。当时开封府的推官韩绛提出,把冷青留在外边,一定还会迷惑群众,扩散不好的影响。担任翰林学士的赵概提出,如果冷青自称皇子,并非欺妄,那他就不是骗子,就不该判处流放编管之罪,而应为之正身,告知天下;

相反,如果冷青确是进行诈骗,那么流放编管的处分也太轻了,应该从严判其欺君之罪,立即处死。仁宗皇帝觉得此事关系到自己的名誉,就下旨命令赵概同包拯一起彻底查清冷青之案,弄个水落石出!
冷青案件表面无头无绪,好像甚为复杂,但实际上最重要的线索只在冷青的母亲身上。包拯同赵概一起审理冷青,经过几次反复,盘根究底,使案情逐步得到澄清。

原来,冷青的母亲王氏,确实曾在宫中当过宫女,后来,宫里放出一批宫女,让她们归回老家,王氏就是这样离宫的。随后,王氏嫁给医生冷绪,冷青即是她所生。
包拯和赵概掌握了一个最关键的情节,就是冷青的母亲离宫出嫁后,生的第一胎是个女儿,第二胎才生了冷青。这样一来,一场大骗局就被彻底揭穿了!

至于金大道和尚,在审理中也得以查清。金大道原名叫高继安,是一个曾经作恶而被开除的军人,被发配鼎州(今湖南常德市)。

后来他打通关节,假装有病,免除了发配之罪。出狱后,他打扮成名山和尚的模样,到处“谈经说法”,信口雌黄,招摇过市,专门结交当朝的达官贵人,骗取钱财。

终于,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冷青,并将他巧加利用。他明知冷青是个骗子,反而故意结交,一同行骗。待冷青被抓,他又出主意让冷青装疯卖傻,结果蒙混了开封府尹钱明逸。钱明逸没能审出此案,在公堂之上为骗子起身施礼,有失皇威,再加上开封府又出了其他一些过失,结果遭到罢官,以龙图阁学士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包拯同赵概两人审清冷青案后,上疏皇帝,将冷青与高继安处于极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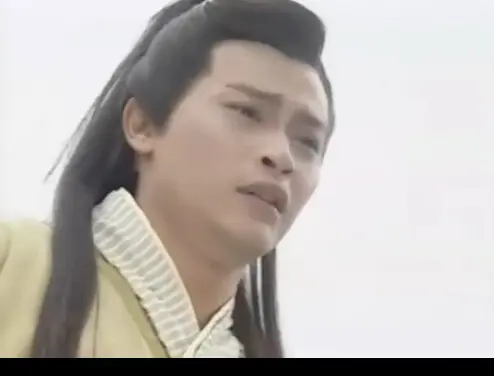
轰动一时的皇子案,就此了结。

包拯审理假皇子的案子在民间越传越神,越传越离奇。

但是,这个假皇子只是社会上的一个小混混,行骗的手段并不复杂,行骗的目的也很简单。于是,人们就将宫廷里的事添油加醋地掺和了进去,慢慢地故事的中心转移到宫内,围绕着宫内的重大问题展开。
第二件事就是《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中记载的仁宗母子生前不能相认的故事。
这段历史记载基本可信。

宋仁宗的生母李宸妃初入宫时,为真宗的皇后刘氏的“侍儿”,性情庄重寡言,真宗封为“司寝”。李宸妃22岁怀孕。此时真宗已43岁,刘皇后41岁,一直未生育。不久,李宸妃生一男子,就是后来的仁宗,刘皇后则妄称为己子。真宗晚年多病,“事多决于后”。仁宗13岁时按真宗遗昭即位,“尊(刘)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李宸妃“黑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生也”。

刘后性警悟,晓史书,临朝称制11年,“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此间差一点儿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女皇帝。那些专事逢迎拍马之辈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太监程琳亦献《武后临朝图》,但都被刘后严词拒绝。

后来,刘后虽夺了李宸妃之子,却没有加害之意,直至李宸妃病逝时,她还听从大臣吕夷简之言,厚礼葬之。

至刘太后病逝,仁宗才听燕王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

仁宗得知极为哀痛,下诏“尊宸妃为皇太后”。母子一生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认,可算是莫大的悲剧!仁宗内心的创痛,我们可想而知。

一个贵为皇帝,一个却是先朝的妃子深居冷宫,孤苦伶仃直至死去。而这一切都是刘太后一手造成的。

后有为仁宗鸣不平者,根据这一段史实编撰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终让刘皇后得到报应,李氏与仁宗母子终于相认,让这千古冤案得以圆满结局。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毕竟与史实相差甚远。

李宸妃被尊为皇太后时,一些臣僚上书仁宗追究斥责(刘)太后垂帘时事,但右司谏范仲淹对仁宗说:“刘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仁宗认为这是识大体、慰孝思之言,采纳了这个意见。以至此事在当时没有形成公案而掀起大的波澜。
从史书上看,刘后很能干,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而编进狸猫换太子故事中的刘贵妃,却是个狠毒奸诈的女人,但这个故事中的刘贵妃却很容易使人想起仁宗身边的另外一个女人——张贵妃。她善于心计,干预朝政,很不得人心。
这第三个事件就是张贵妃的“红伞事件”。
作为皇帝,仁宗在生活上很有一些花花事儿,算是“好戏连台”。他即位没几年,就宠上尚美人、杨美人,又听信谗言,废了郭皇后。后来被两位美人弄得神魂颠倒,身体消瘦,甚至有时神志不清,无法理朝。朝臣都为皇帝的健康着想,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让大宦官阎文应把这两位美人撵出宫去了事。再后来,仁宗就宠上了张贵妃。张贵妃善于心计,不但“宠冠后宫”,而且“势动中外”,干预朝政。北宋一向比较注意不许以后妃为首的后宫干预政治,除了皇帝年幼、皇太后名正言顺地摄政外,均不允许后妃公开勾结朝廷上的政治势力。但张贵妃却成了例外。她的地位低于皇后,可在礼仪方面她往往逾越当时的制度,想同皇后等齐。她要求打红伞,增加卫兵人数,这在宫内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和反对。包拯当时在千里之外为官,并不在宫中,自然也就没有对张贵妃挡驾指责之事。显然,后人把自己的感情和期望寄托在包拯身上,在编讲狸猫换太子的案件时,加进了贵妃打着皇后的仪仗出宫从而引出包拯打銮驾的一段故事。

假皇子案中的“宫女流落民间”、宋史中的“刘后夺子”,以及张贵妃的“红伞事件”,都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得到反映,并且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才有了李妃拦轿告状、刘贵妃狸猫换太子,以及包拯打銮驾等故事。
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原形”。如刘贵妃的专横、仁宗的怕包拯等,均在史料中有所体现。
张贵妃之死引发了朝廷之争,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真实,那是很有趣味的。
张贵妃死后,仁宗十分伤心。他对朝臣们说,张贵妃很有功劳,过去颜秀等人进行宫廷阴谋的时候,她曾挺身保护仁宗;又说当大旱之年,张贵妃曾在宫中祈雨,并刺臂出血,用血书写祝辞。仁宗说,她的这些表现,可惜宫外都没有人知道,应该为她追加荣誉。
朝廷之上多的是拍马逢迎之徒。仁宗这番话一出口,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应该用皇后的礼仪在皇仪殿治丧。按理讲,此事应与宰相商议,但宰相陈执中是个一味逢迎的人,一点也不能坚持礼法制度。于是,近臣与宗室都入皇仪殿祭奠。
按照礼仪,贵妃相当一品官阶,死了之后,皇帝可辍朝三日以示哀悼。但大臣们投仁宗之所好,建议辍朝五日。最后,仁宗自己决定辍朝七日。这样的决定自然招来某些人的反对,但仁宗根本不予理睬。在宰相和宦官们的合谋下,死了的张贵妃终于被追册为皇后,赐谥“温成”。这些对于死人的恭维,其“现实意义”完全在于讨好仁宗。
但朝中亦有耿直之臣,才使这一闹剧更显得热闹非常。张贵妃起先的谥号是“恭德”,但遭到强烈的反对,后又改为“温成”。张贵妃之死,京城禁乐一月,一切仪式按照皇后的标准办。就在出殡临葬之时,有个宣读哀册的仪式,起先叫枢密副使孙沔担当这个角色。但作为执政官之一的孙沔是一个不肯迎合的人,他上奏说:“章穆皇后举行丧礼,皆用两制官(指翰林学士和知制浩,翰林学士为内制,知制浩为外制,今称两制官)行事。现今温成仅是追谥,反而命令二府大臣行事,这不可以。”他捧了哀册在仁宗面前坚持理由,并且还大声说道:“以臣孙沔读册是可以的,以枢密使读册是不可的。”说罢,把哀册放置起来就退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宰相陈执中,居然拿起哀册,自己宣读起来。孙沔由于反对追册温成皇后,被罢职,出知杭州。
在举行过丧礼之后,还要替张贵妃立小忌,由于遭到激烈反对,才算作罢。后来还就温成皇后的旧室立庙,并规定四时享礼的制度。又把温成皇后所葬之处题为“温成皇后园”。当时刘沆也当上了宰相,任了温成皇后的监护使和圆陵使,但这又遭到御史中丞孙抃的反对,并在仁宗面前公开争论起来。类似的情形一幕又一幕地在朝廷上演:谏官范镇向仁宗上奏:“太常议温成皇后葬礼,前些日子叫温成园,随后又改叫园陵;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这些都出自礼官,前日是则今日非,今日是则前日非。古代法吏舞法,今天礼官舞礼。如果不加诘问,恐怕朝廷的典章逐渐败坏而不可挽救。陛下应查处礼官,以正中外的疑惑与争论。”但伤心过度的仁宗皇帝,是不会理睬这样的意见的。

但事情逐渐发展为弹劾礼官事件。礼院的书吏纷纷畏罪潜逃。结果使两个比较正直的人遭到惩罚。一个是同知太常礼院吴充,一个是太常寺太祝鞠真卿,分别贬知高邮军、淮阳军。台谏官们对这种贬非其罪的事情大为不满,都出来说话。冯京当时任太常丞,因上疏讲得十分恳切,引起宰相刘沆大怒,结果,也遭到贬官。
仁宗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大动肝火,朝中大臣围绕一个女人而大做文章,把朝中政治弄得乌烟瘴气,最终这个责任还要归到仁宗身上。这番闹剧上演时,包拯恰在千里之外。如果坚持正义、敢于直谏的包拯还在朝中,那他会怎样做呢?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样的呢?
千百年来,多少人猜测着、想象着、编造着。一个个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曲折而又生动的故事由此生发,而最典型、最完美的编造,要数人们世代传讲的这则千古奇案——狸猫换太子。
包拯力阻张贵妃为张尧佐要官,这在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事的。

在狸猫换太子的案件中,连皇帝也怕包拯几分,这也是事出有因的。据史书记载,皇帝宠爱张贵妃,听信谗言,一直想为她的伯父张尧佐封大官、加厚禄。为此包拯多次弹劾,弄得皇帝有点害怕。结果,皇帝的这一旨意未能完全实现。对此,朱弁所写《曲洧旧闻》中记载道:“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上。久之,以上温成(按:即张贵妃)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这完全是皇祐二年延诤的真实记载,包拯竟敢在皇帝面前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而皇帝竟然能耐着性子听,并采纳他的意见,可见仁宗皇帝对包拯确实有点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