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石怀玉惊梦》中石怀玉的心理特征变化及表达
《石怀玉惊梦》原是传统大戏《峰翠山》的一折。讲述了武孝廉石怀玉进京赶考,突发疾病遭遇土匪,幸得莲娘吐珠相救,二人结为夫妻。后高中状元被王丞相招为东床,恩将仇报杀死莲娘。在梦里莲娘化为冤魂索命,对石怀玉进行逼问、恐吓造成精神打击。石怀玉在醒来后因无法承受精神压力,暴毙而死。本剧在主题上充满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动作技巧上运用了灭烛复明、变脸、倒硬人等表现手法,把石怀玉这一形象刻画为川剧小生经典,再经过蓝光临、肖德美一代代大师的演绎、修改,使其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这出戏为川剧传统戏,原名为《活捉石怀玉》。后经过蓝光临先生的改编、推广,将其情节做了一定优化,将其推上舞台,成就了此川剧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蓝光临,著名川剧小生演员。1988年在京城首演《怀玉惊梦》的时候,蓝光临丰富的身段表演和精彩的唱词赢得满台喝彩,戏剧评论家胡沙称其“一曲惊梦惊北京,好似当年魏长生”。他十岁登台,一生会戏颇多,更是川剧改革的先锋人物,是川剧乃至中国戏曲史上无法被忽视的一位大师。

在开场的“西风起淡月色”唱段中,石怀玉用自我剖析的方式叙述了杀害莲娘的前因后果。因这出戏常常以折子戏的方式从大戏中剥离出来单独演出,因此需要这样一种回顾的形式缝补折与折之间断层,用以交代情节。从石怀玉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一个忘恩负义、小人得势的伪君子形象。他甚至对于自己的言行颇为满意,丝毫没有道德的负罪感。认为自己才是不幸的那一个,把一切得益于老天爷的相助:“可怜我命休也,石怀玉声声呼唤老天爷”。然而之后莲娘的复苏,完全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他的心理防线随着剧情的推进正在一步步崩溃。

一、“本我”与“超我”的对立
石怀玉为什么会死?导致其死因的到底是由于他对于自己所作的愧疚还是因为对于胡莲娘的恐惧?在旧戏名“活捉石怀玉”、“莲娘索珠”中,对石怀玉死因的解释应该偏向于后者,即是由于胡莲娘“活捉”、“索珠”的行为而使他受到恐吓而死。在改编后的新戏名“石怀玉惊梦”,明显发现动作主体回归到石怀玉身上。两版戏名的不同,体现对石怀玉死亡原因的不同阐释。笔者尝试用弗洛伊德的人格三结构来对此进行探讨。
弗洛伊德曾提出过“人格三结构说”。他认为,人格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它由三个子系统构成,即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本我,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驱使自“快乐原则”,追求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并得到发展的那一部分,遵循“现实原则”但不意味着废除快乐原则。仅仅是迫于现实而暂缓实行快乐原则。超我,即“道德化了的自我”,受“至善原则”支配,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部分构成。自我理想表现为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良心则意味着对违反道德标准行为的惩罚。“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和发展来的,是接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石怀玉的“本我”在于喜新厌旧却又不能摆脱莲娘的纠缠不休的憎恨和对胡莲娘是“女流之辈”的身份却比自己更有能力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下的嫉妒。这些意图导致了他的忘恩负义,从而做出“手持钢刀把他头首切”的行为。而胡莲娘为狐精的事实,是石怀玉杀妻的直接理由。石怀玉的“超我”一直隐藏在内心,直到胡莲娘化为鬼魂来向石怀玉索命,这才意识到在道德准则上,自己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他醒来之后陷于两种意识的对抗,没有一个“自我”来协调“本我”和“超我”的冲突,以至于把“海棠”认成“莲娘”,把“侍女”说成“石怀玉”。可见这时候其内心矛盾斗争激烈,精神不能在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中平衡,以至于被矛盾生生撕裂开来,气绝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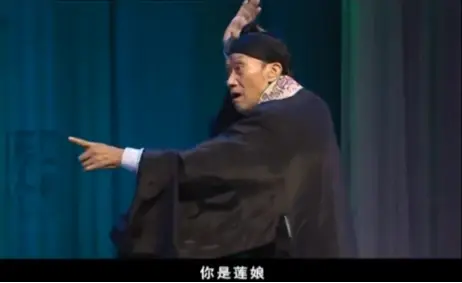

二、从阶段性变脸看石怀玉心理特征变化
在本剧中石怀玉一共有三次变脸。出场时的石怀玉粉面含春,一看便知是一个高中状元,又打得胜仗的得意将士。在帮腔唱到“亏心事儿做不得”时,石怀玉左右堤防,以及鼓声模仿风声时紧张地转头才体现出他做了亏心事的小人模样。他在听到风声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表现恐惧,而是提刀准备自卫。武将出身的他不至于完全丧失理智,但还没达到能清楚反思自己过错的程度,他的反映体现他的第一直觉是提刀反抗,认为人能斩妖,也能斩鬼。

第一次变脸在莲娘与拿鬼将石怀玉的外衣扯掉,露出黑褶子时。他惊吓至极,转身一个谷灰草抹脸,体现极度害怕和狼狈之状。知道自己不敌鬼怪,这时他的心理由警惕到恐惧,与先前的光鲜亮丽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这里的黑脸是一种象征的手法,即将人物的抽象的心理状态具象化,表现为满脸漆黑。中国戏曲的虚涵性便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是一种相当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

第二次变脸在石怀玉梦醒之时。他拿着帽翅疯疯癫癫地跑出帐来,先前梦里的黑脸已经抹去,呈完全卸妆状态的清水脸。面带蜡黄,眼神空洞无力,神情恍惚。此时的石怀玉已经有了认知功能障碍,连侍女和自己都分不清楚了。他的心理变化由恐惧转向崩溃,内心的“超我”也在一步步苏醒。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过为时已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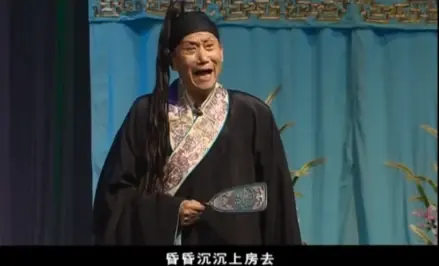
第三次变脸是在帮腔唱出“你就是当今的活王魁”时的气绝脸。石怀玉听到四处传来鬼魂索命的声音,一个背壳摔下去,在帮腔的指责下,变出气绝脸,倒硬人一气呵成,代表着这个角色的死亡。戏剧表现的夸张性在这里体现出来,石怀玉临死前舞台四处擂鼓齐鸣,夹有帮腔的呼声。这呼声即可以理解为舞台上抽象化表达角色内心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审问,也可以理解为他听到“鬼神”呼喊他的名字。

在中国戏剧起源考证的“巫觋说”一派认为,戏剧的起源就是祭祀鬼神的仪式。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他认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鬼神在戏剧中扮演的作用不可忽视,《怀玉惊梦》里也正是鬼神的外力介入真正改变了他的道德观、价值观。“勾魂”实名为勾魂,实际上是自己对未知的恐惧反噬自己,最终落得死亡的下场。

三、石怀玉对于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
纵观全局,在石怀玉醒来之后的一段表演尤其值得琢磨。这一段的人物情感表达、心理表达、动作展示十分写意。首先听到帮腔唱“一场噩梦一场惊,孽债未还苦煞人。”石怀玉跌跌撞撞走上台来,有气无力又带有一点委屈地说:“昏昏沉沉上房去。”他的自我意识还是有的,只是认为昨晚的噩梦吓人,想要上房找夫人寻求安慰。从他碰到海棠后,听错名字,脱口而出“你是石怀玉”开始,他的自我意识发生了暂时性隐退,而之后的表演中,自己都是“莲娘”的化身。他对着海棠说,“昨夜晚你将我灌醉,冤杀莲娘好伤悲”“香魂一怒化冤鬼,今夜晚要把尔的狗命追”,这些显然正确的主体双方应该是莲娘对着石怀玉说的话,全被石怀玉一股脑抛给海棠。显然他的心理自我已经转变,是把自己作为莲娘、海棠看作石怀玉,对她发泄、指责,也俗称“鬼上身”。
在最后一系列的踢褶子高飞跪甩水发的表演后,石怀玉听到四周索命声传来,再一个高背壳,后开始以第二人称视角说:“石怀玉!你犯了弃旧迎新冤杀糟糠的滔天罪啊”,这里是和观众的一个小互动,再次体现了戏剧表演的灵活、丰富。他指向观众,实际上是在说自己。舞台此时犹如一面镜子,反射出石怀玉的自我意识,亦让观众告诫自己。可以说,这一句让石怀玉走下舞台、走出剧本,进入了普普通通大众之间,拉近了虚构角色与真实个体之间的距离,这一步设计地极为巧妙。

四、总结
在石怀玉“本我”与“超我”的对抗中,他迷失于道德的伤痛;在莲娘与怀玉的斗争中,他嘴硬、抵制,却无法说服自己,终于是在对自我的追问中,沦为私欲的献祭品。石怀玉人格的双重性表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纠结。戏剧表现形式的多样、丰富,体现了传统艺术的包容、虚涵。川剧正是从舞台上角色的善恶转变中,把道德观念传递给观众,把真善美教化给更多人。要论本部戏精彩的部分,主要有三处,一是开头“徒歌”形式的经典90句唱词,一步步描写出石怀玉的病态心理特征;二是莲娘和怀玉的斡旋,从“灭烛复明”到“鬼扯脚”,即是人与鬼的斗争,也是恶与善的斗争;三是石怀玉醒后人格的转变,观念新颖,当之无愧的先锋派表演。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出戏都将石怀玉的心理特征刻画地准确、深刻。《石怀玉惊梦》是百年川剧沉淀出的精萃,也是世界诸多戏剧中的翘楚。

参考文献:
[1] 川剧《石怀玉惊梦》蓝光临、陈巧茹
[2] 王宬葓.川剧高腔音乐中的对比复调探究[J].四川戏剧,2015(05):53-56.
[3] 付贵.谈川剧高腔的飞句及犯腔[J].四川戏剧,2015(04):131-133.
[4] 雷晶晶.《窦娥冤》与《哈姆雷特》叙事美学之比较[J].巢湖学院学报,2019,21(02):59-66.
[5] 原一川,王娟.从弗洛伊德的人格三结构阐释哈姆雷特的犹豫[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6):141-144.
[6] 张学君.传情达意 悦耳动听——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蓝光临的艺术境界[J].文史杂志,2013(06):50-52.
[7] 万平,马丽.川剧名家蓝光临访谈录——《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成都卷)》之蓝光临篇[J].四川戏剧,2012(01):16-18.
[8] 黄光新.技艺精深的蓝光临[J].中国戏剧,1990(03):25-28.
[9] 王朝闻.体验重于体现[J].瞭望周刊,1990(0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