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 翻译】蝎子中文名命名的感想

关于中文名命名的专栏已经发过很多篇了,今天是想表达一下各种学名的翻译感想,不过还是以学名、译名的各种问题为主要内容
本人主张根据词源学给蝎子制定中文名,采用的是译名法命名,所以如果是直接照搬文献名的懒人,或者是自己另外取俗名的人,又或者是跟风不动脑引用别人的俗名的人,和我的方式没有任何可比性。
尤其是第一和第三类人,不好意思,真的跟我完全不是一个维度,这些名字都是别人取的,你只是在用别人的名字,你没资格跟我抬杠。至于第二类人,也就是自己取俗名的人,我认为虽然我反对你的方式,认为你的方式不具有远见,容易造成误导,分类不清晰等等,但是你比第一和第三类人好不少,最起码你也是跟我一样自行取名,起码也是有思考的,所以比起那两类人我相对愿意尊重你。
但是就事论事,出于商业噱头而取的俗名我不会尊重,如果只是没有像我考虑得这么多,就随便取了个名也情有可原,毕竟大部分人的见识和认知都是局限于现有流通种,在这个范围内取不会造成混淆的俗名也很正常。但是很可惜,大部分俗名要么只是为了显得牛逼点,要么是有各种混乱造成误导,就这类情况而言,我反对俗名。
有一些俗名,暂时没有混淆,但是由于它们和大部分俗名一样,是以“地名+颜色+外形”的模式定名的,很容易和未来可能的流通种混淆。很多同属的物种难以以直观的外形制定相异的名字,所以我认为另取俗名不具有远见,产生混乱的几率更高。俗名的问题在本文不多提。
所以,如果是第一和第三类的无脑跟风杠精,该滚多远滚多远;如果是第二类人,也可以选择看或不看,接不接受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每个人观念不同,就好比我也不接受俗名一样,这就是求同存异。
本专栏仅欢迎接受译名思想的人,爬宠圈的著名up主怪兽无敌z也经常来问我怎么翻译某个学名,可见虽然对方主要以饲养为主,但是也不代表就要和学术问题割裂。学术和饲养从不冲突,反而饲养包含于学术。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养的是一个生物,学术是研究生物,饲养也是研究生物,只不过饲养主要仅限于发育这一条分支而已。
对学名的看法
如果有人不了解,那么在此重申一下,“学名”仅指“拉丁文名”,“中文学名”这种词只有门外汉会用,但一般指“中文正名”。“中文名”可分为:译名(学名中文)、俗名、文献名(中文正式名)。
不得不说的是,学名和俗名的制定方法本质上相同,只不过学名中还会有很多以人名命名的,而和俗名一样以形态和产地命名的则更是屡见不鲜。至于产地命名,通常情况下都是以模式产地(即首次发现该物种的产地)命名,而俗名中的地名,则只不过是在一堆产地中随意挑选了一个,又或者是根据流通者的那一次的采集信息。可见,俗名中的产地名意义远不如学名,但是无论是俗名还是学名,都不要以为这个物种就一定只产自这个产地。
在以形态定名时,学名和俗名会产生的问题也很近似,这主要归因于该物种的发现年代。以形态命名的蝎种,这个形态极有可能出现在其它类群或是同属的蝎子上。这种情况就是,当初只知道这个物种有这个形态,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发现了新种,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形态,这是受了解程度所限。
例如Diplocentrus属,译为“双棘蝎”,学名以其尾刺上的副刺瘤(subaculear tubercle)命名,代表这类蝎子有两根尾刺,该属建立于1880年。

该属隶属于Diplocentridae科,当时作为了scorpionidae的亚科,现独立。就不说同科的其它属了,例如Kolotl、Cazierius、Tarsoporosus、Nebo属等等,这个科的所有属都有副刺瘤的形态。



而甚至在其它科里,也同样有这个结构,例如Buthidae科下,建立于1972年的Reddyanus属,从年代来看,显然是比Diplocentrus晚。

但是同样也有早于Diplocentrus属的属,例如1836年的Tityus属,模式种为scorpio bahiensis Perty, 1833,这个种也是有副刺瘤的。(不过并非Tityus属所有种都有副刺瘤(图2))


所以如果要抬杠的话,就会有人说,为什么只有Diplocentrus能叫双棘蝎,明明别的属也有两根刺啊。这就回到了之前的问题,首先是认知深度的问题,当人们第一次发现Diplocentrus时自然就把它们这么命名,虽然之后发现了同科的其它物种也具有相同的形态结构,但因为存在其他差异,肯定是要分成不同属的,既然是不同属,那就是不可能给予同样的名称的。
而如果要以命名时间更早的Tityus属为例,那就是因为分类学的问题,是因为Diplocentidae科当初是视作scorpionidae科的亚科,也就是说它是被看作一类scorpionidae科的蝎子,从该科中细分出来的,而所基于的特征,就是毒囊上的第二根刺,这是同科的其它亚科没有的特征(现在Diplocentidae是独立科了)。所以说这个“diplocentr-”当时是用以区分其它scorpionidae科的亚科而定的学名,范畴局限在这个科内,并没有跟全世界的蝎属比较。
虽然学名存在着与俗名一样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学名的命名,都会注意特征的区分。除了个别种的命名,不得不承认,是真的无脑。
例如2019年命名的Pandinurus fulvipes(图1),种名所要表达的意思是“黄脚”,但是这个特征也完全符合1896年同属的Pandinurus phillipsii(图2)。不过最起码,在翻译时不会有冲突,只不过是把“黄脚”一名给了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更晚命名的物种而已。


我见过最无脑的学名,那就是2012年的Heterometrus atrascorpius,种名的意思是“黑蝎子”,我寻思这个属明明一大堆都是黑色的,而且就算和模式种比较也是黑色的,为什么还能以不具有任何区分性的整体颜色来命名?

“你咋这么牛逼呢学名都敢怼?有本事你取个名啊”
根据配图及文字描述,在我看来该种的最大特征是成体也有着白色的毒囊,所以如果要我命名,那我就会叫Heterometrus albivesicalis。
我敢怼,我肯定有自己的理论。我不是那些口嗨键盘侠,只会反对却没半点主张和看法。


可见,学名中的无脑命名自然是有的,而冲突命名可能归因于年代和分类,这点情理之中。甚至还有学名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Cercophonius、Phoniocercus和Urophonius,全都是“尾巴”+“屠杀者”两个词根组合构成,所以译名会冲突。但是拉丁文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根据拼写区分,这也是为什么直接使用拉丁文是最好的原因之一。
有一些属名可能会存在分类学上的误导。例如Uroctonus属隶属于Uroctoninae亚科,但关于该亚科应置于哪个科目前尚无定论。而在Vaejovidae科中,则出现了例如Paruroctonus属,那么会造成让人以为这两者亲缘关系一定较近的误导。同词根的学名出现于不同分类显然是因为研究的深度造成的,可能当时从外形来看很近似,因此以同词根的学名命名,但是现在逐渐以分子来确定系统发育关系,自然有可能推翻当时的结论。研究是会发展和完善的,错误是正常的,但很可惜我没见过会因为这种分类不当而更改属名的。
总结下来,学名和俗名一样,有产地命名,但是产地是模式产地,有一定意义;有形态定种名,有些很直观的形态很可能出现在同属的其它种中,有形态定属名,这个形态也可能出现在其它属中,这两种会有冲突的形态命名是归因于认知程度和这些类群当时的分类;学名也有和俗名一样有意思相同的不同属或种,但是可以根据拼写区分,而俗名则不是,也并没有试图减少冲突,完全相同的中文字会出现在一堆不同属中,例如“金蝎”,至少出现在了14个不同属的俗名中。
俗名中有很多以错误产地命名的蝎种,例如Hadrurus arizonensis的"pallidus"色型并不产自佛罗里达,缺被叫做“佛罗里达沙漠金蝎”;又如Uroplectes属,俗名无脑地将所有种都以“纳米比亚”命名,然而以其中一个为例,U. flavoviridis就根本没有纳米比亚的分布。
例如Heterometrus indus,其种名为印度,但是该种后来发现实际为斯里兰卡特有,因此学名也可能存在误导性,这样一来翻译的译名也会“继承“这个误导,此时如果有可能,那就可以选择变通。但因其曾经的两个次异名,scorpio ceylonicus和Heterometrus spinifer solitarius,其中前者种名是“模式产地”锡兰,而这个样本实际是H. serratus,因此不能译作“锡兰异距蝎”;而后者亚种名为英文中的solitary,我没看过原文献,并不明确是指最初只有一个单一的模式样本,还是指该种在野外的分布非常零散,从未有群居情况被发现。因此也不能译作“独模异距蝎”或者“隐士异距蝎”,故我目前仍只能将其译作“印度异距蝎”。
学名的问题多是归因于认知,俗名自然也是。但是,俗名并不是因为某个物种还未发现,而是因为制定这个俗名的人并没有去了解过其它已知种。那么既然此时俗名是晚于学名而命名的,就完全是可以做到降低冲突的。也就是说,如果要以形态定名,那只需看有无相同形态的种或属便可预防冲突。
但我觉得另取俗名实在是很麻烦,如果局限于饲养圈,我会考虑到未来会不会有新流通的已知种,那么如果对于现在流通的某个已知种随意命名,则很可能与未来的产生冲突。注意,这和学名不一样,的确,毕竟没人有“未来视”,命名学名的人也想不到以后会不会有在这个特征上一致的新种,但是俗名所应用的那些种,仅仅只是已知种中的冰山一角,虽然的确也没法预料未知种,但最起码能做到不和所有已知种产生冲突。
我以前也一直说,我最初也是都用的俗名,然后自己整理图鉴,看到未有中文名的,就模仿俗名的命名方式定名,然后看的种类越来越多,就发现这种方式非常不合适。就比如Hottentotta jayakari,俗名叫伊朗黑尾鳄背,但是下面这种同属的,也在伊朗,且仅在伊朗,也是黑尾,甚至也是黑爪(虽然前者的俗名未加入“黑爪”这个特征,但是是有的),那么按照俗名的命名方式又该如何取名?伊朗黑爪黑尾鳄背蝎?那为什么具有相同特征的H. jayakari就只叫黑尾呢?

另外在其中一篇过往专栏中,我最后特意列举了一大堆同属的高度近似的物种,这些物种很多有产地重叠,因此按照产地+形态的方式定名是不可取的。
所以到后来,我就开始根据学名本意来定中文名。
个人的中文名制定(新)
以前总是有人说俗名便于记忆、便于流通,我寻思这完全是胡扯。我自己在命名译名的时候会注意很多和简洁性相关的问题(详见后文),但是俗名可不是,长串的俗名层见迭出,就是把地名+各种特征+修饰词+噱头往上堆砌,完全就只是听起来很通俗,但究其简洁性则为零。
一个译名记不记得住和诸多变量有关,第一、是否排斥这个名字(新人不懂,但和我作对的那些跟风孤儿是,如果排斥了,那什么都不用说了),第二、商业圈和饲养圈的流通频度(决定了使用者的数量,也就是客观环境对主观的潜意识影响),第三、对该种蝎子的喜爱程度(决定了主观使用该名的频度,记忆深刻度随使用频度上升,当然前提是不排斥)。
就这么说吧,世界上2000多种蝎子你想全部以俗名方式命名实在是痴人说梦。对于学术问题我倾向于统一原则,既然另取俗名做不到命名全部蝎种,那就干脆翻译译名。国内文献名就别想了,有译名有俗名有译俗结合,没法达到我统一的目的。
我的翻译模板一直在完善,就如同专业学者对一个类群的认知一样,完善度取决于了解的多少。







总之,在翻译学名时,我既会考虑要表达原意,又会考虑简便度,还要尽可能统一规范。所以当学名中出现人名时:属名为以现代人名的单一形式出现,以“氏”的模式定名,与其它属结合,音译全部人名;属名为神话人名,以身份定名;种名为现代人名,以“氏”的模式定名;种名为神话人名,音译全部人名。
就仅看我个人图鉴里收录的蝎种,就已达1000多种已命名中文名的物种,其它我命名过的都出现在专门的介绍专栏里,但是要么缺图,要么图的质量太差,所以没收录进去。
其实翻译了这么多学名后自然也有了经验,很多常见的词缀一看就知道该怎么翻译,种名是人名的时候直接首音节+氏就完事了,确实让我感觉挺无聊。像那种flavimanus啊brevicauda啊,一看就知道一个是黄掌一个是短尾,对词根的熟悉度已经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因此只有那种奇奇怪怪的种名才会引起我的兴趣,就比如当地语言命名,一般都是很奇怪的拼写,会让人好奇地去看文献中提供的词源学。
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也就是那种并非常见特征,并且做到简洁和顺口需要稍微动一下脑子的。
例如Heterometrus spinifer,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叫“多刺异距蝎”,当时只注意到了spini-这个前缀,后来才知道-ifer。所以这个种名实际意思是“带有棘刺的”,那么“有刺异距蝎”、“带刺异距蝎”在我看来不是很好听,于是我就想近义词,想到了“携带”,进而命名成了“携刺异距蝎”,至少我觉得比较好听。


Hadogenes paucidens,种名意为“稀少的齿”(注意这个paucus本意不是小,而是指数量少),虽然我没看过原文献,不知道它指的是螯肢(口器)上的齿突还是螯指(钳子)上的齿突,我将本种译作了“寡齿冥神蝎”。


Uroctonus mordax,种名意为“蛰刺”,结合同词根的mordacity,我译作了“辛螫尾戮蝎”,指其的蛰伤会造成剧痛,不过本种的毒性是很低的。



Teruelius annulatus,种名意为“用指环点缀的”,所以我就译为了“缀环特氏蝎”。


Megacormus segmentatus,种名意为“以边界装饰的”,segment本身是“切割分化后的一节节或一块块的部分”,而“atus”是常见的意为“装饰”后缀,在前面的“annulatus”里就有,我将本种译作了“饰缘硕躯蝎”。


Centruroides limbatus,原本我是参考了Carcharhinus limbatus的中文名“黑边鳍真鲨”而叫的“黑边似刺尾蝎”,后来了解深入了,知道了这个种名仅仅是“边缘化”的意思,而种名中没有例如nigro等意为“黑色”的前缀,因此译作“黑边”有一定跳跃性,故译作了“缘纹似刺尾蝎”,这里取了浅色种便于观察条纹。


过往专栏
已有更新,仅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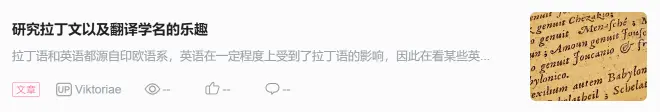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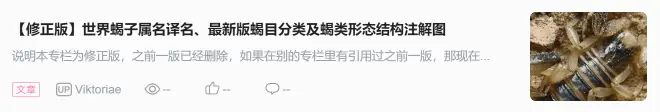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