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之马》有感
“1889年的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希·尼采走出卡洛阿尔贝托街6号的大门,也许是去散步,也许是去邮局拿信。离他不远处,或实际上离他很远的地方,一个马车夫正和他那倔强的马较劲,不管他怎样驱策,马就是纹丝不动。于是,马车夫朱塞佩·卡洛·埃托雷不耐烦了,挥起鞭子向马抽去。尼采走近围观人群,制止了这残忍的场面,马车夫此刻已气得七窍生烟。身材魁梧,蓄着大胡子的尼采突然跳上马车,甩开胳膊抱住了马脖子,开始啜泣。邻居把他带回了家,他在矮沙发上躺了两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直到最后喃喃道出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真傻。在母亲和姐妹的照顾下尼采继续活了10年,脾气温和,神志不清。至于那匹马,我们一无所知。”
这便是《都灵之马》的引子。似乎奠定思想,与尼采相关,与“上帝已死”相关。
尼采抱马发疯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上述这一事件的即兴而起,也可能是其在1887年第一次阅读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
在梦境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曾目睹一个醉醺醺的马车夫,不断鞭打不胜重负的瘦马。当路人见到如此情形时,有几个人也拿起了鞭子,也开始抽向那匹马,并高呼着,吹着口哨,嘿嘿笑着朝它的眼睛猛抽,拉斯科利尼科夫泪流满面,大声叫着,不顾鞭子打在自己脸上,抱住那匹奄奄一息的马,可是那些抽马的人不但不停下酷刑,反倒高喊着,“杀死它!” 终于结束了那匹马的生命。
在其对友人的信件中,似乎也曾提到其对这一文段的重视。这似乎在几个月后的都灵得以应验......
影片共六个章节,以黑底白字“第x日”的形式来割裂,步入下一章节。
狂风,尘土,吹荡在画面,父亲驾着羸弱的老马缓缓行进在路上。没有生机,没有语言。有的只是压抑的氛围与无休止的劲风。
第一日
马厩:父亲牵着驽马回来,女儿急匆匆的收拾马车,喂养驽马。
室内:父亲似是右手拥有残疾尚且不能自己脱衣穿衣,站在床边等待女儿的帮助。女儿则帮助父亲脱衣脱靴,穿衣穿鞋。而父亲在脱衣后无神的躺在床上,似在睡觉,似在思索。镜头切到女儿,女儿在帮父亲换衣后便去煮土豆,在煮土豆的间隙便在窗边静坐。视角也随之改变。由可以看到女儿的侧面摇到只能看见女儿的背面。女儿背影的时间很长。时间长到土豆已被煮熟。
餐桌:从正面拍摄父亲吃土豆。从盘里的土豆的特写,摇到苍老的单只左手捏碎滚烫的土豆的特写,摇到满是胡髭的脸部吃滚烫土豆碎块的抽动的特写。父亲的右手有残疾这一体现的更胜,父亲吃土豆的样子饥饿、急切甚至慌张,不时抬起无神的眼睛看看女儿。在慌张的吃完土豆后,便坐到窗边静坐。
室内:女儿在洗漱之后便熄灯睡觉,以及父亲关于“蛀木虫”的谈话。“蛀木虫”的离开,似乎是世界崩坏的开始。
第二日
室外:女儿出门打水。
室内:女儿帮助父亲穿衣,取出还剩半瓶的白兰地,父亲小酌一口。女儿洗脸,帮助父亲穿上大衣。
马厩:女儿拉出马车,父亲牵出驽马。驽马停止工作。父亲强势的用马鞭抽向驽马,女儿出言阻止。把驽马和马车推回马厩。
室内:父亲气急败坏的脱下外套。女儿再次帮助父亲脱衣脱靴,穿衣穿鞋。父亲在不忿的劈柴。女儿则在洗衣服。父亲用单手撑开晾衣绳。镜头切换,女儿去倒掉洗衣热水,父亲在扎着皮带。女儿的一句“饭好了”便结束了父亲的动作。镜头也转移到餐桌。
餐桌:又是吃着单调的土豆,但是镜头则是女儿。女儿吃土豆平和、精致、若有所思,似在感受土豆带来的意义。
室内(远景):在女儿吃完土豆后镜头便切到父亲还是在那个窗边,不过由背影转到侧面,女儿也坐在床上。
有一人推门索要白兰地。并有全片中最长的独白。
一切都毁了。为什么会毁了?因为一切都成了废墟,一切都被侵蚀了,但是我得说是他们糟蹋了一切,因为这可不是那种与所谓无罪的人类援助有关的天灾,正相反,这是人们自己的抉择,关于自身的抉择;当然,上帝肯定促进了抉择,不,我敢说上帝参与了抉择;任何他参与的抉择,都是你能想到的最恐怖之造物。
你懂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沦落,所以我说什么不要紧,因为他们所得万物皆已沦落,自从他们以卑鄙狡诈之法占有万物,就已使万物沦落;因为无论他们触摸什么,都使其沦落,而他们触摸了万物,这就是他们最终的取胜之法,取得那欢天喜地的胜利之法。
占有,沦落;沦落,占有。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换种说法:触摸、沦落,因此占有;或者说触摸、占有,因此沦落。就这样循环着过了几百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就这样,也只能这样。时而隐忍,时而粗暴;时而温和,时而野蛮。这样循环往复着,然而只能仅仅像埋伏着的老鼠伺机出击。
为了这完美的胜利,那一切卓越的、伟大的、高贵的,不应卷入任何形式的纷争,不应有任何形式的抵抗。仅一方的突然消亡,意味着卓越、伟大、高贵的消亡;所以目前统治尘世的,仍是等待伏击的鼠辈。普天之下竟无我们可以隐藏东西的场所,因为万物只要他们能接触到就归他们······
客人的一堆疯话透露出很重要的信息“城镇消失了”这是崩坏的进一步。扔下两个铜板后便拄杖离开。
第三日
室内:女儿起床穿衣。
室外:女儿迎着更加猛烈的风出门打水。
室内:父亲起床女儿又一次帮助父亲穿衣。二人各小酌一杯白兰地。白兰地还剩下三分之一。
马厩:女儿清理稻草,驽马绝食。世界的崩坏。
室内:女儿端来土豆。二人分食,不过镜头是从桌子侧面拍父女俩对称吃土豆的中景。后由父亲长时间的抬头看、女儿随之抬头看引出吉普赛人驾着马车来到的场景。父亲则命令女儿去驱赶吉普赛人。
室外:吉普赛人的马车缓缓驶来。女儿去驱散吉普赛人,不敌反被纠缠,吉普赛人说“和我们走吧”“和我们去美国吧”“你会喜欢那个地方的”。父亲则掏出利斧威吓吉普赛人,其他吉普赛人被其所吓到慌张爬到车上。唯有吉普赛老人给女儿留下一本圣经“这是水钱”后便与其家人离开这里。而吉普赛男人则留下一句莫名其妙的的话“我们还会回来的。水是我们的,地球也是我们的”。
室内:女儿在床上一字一句的朗读圣经。
第四日
室外:女儿迎着更猛的风去打水,女儿折返,来叫父亲。水井干涸了。一点水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父亲则女儿把水井盖上。世界崩坏的更近一步。
室内:父亲独自喝了两杯白兰地。
马厩:女儿的独白,驽马依旧绝食。驽马的无动于衷。
室内:父亲叫女儿收拾东西,准备逃离。
马厩:女儿拉出小车,父亲牵出驽马。小车上装满东西。父亲把驽马拴在车后。女儿在前面拉车,父亲在车旁推车。便在风中艰难的离开马厩。
室外远景:小车随着镜头的拉近渐行渐远,不久便随着镜头的拉远而原路返回。
室外,门前:父亲和女儿一件件的把行李搬回。镜头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女儿坐在窗边看向外面。
第五日
室内:又是女儿在帮父亲穿衣。依旧没有言语。父亲小酌两口白兰地,镜头拉近酒瓶,白兰地所剩无几。
马厩:父亲将门打开,父女二人看了很久的驽马,后父亲将马嚼子取下。女儿将门关上。
室内:父亲坐在窗边看向窗外,窗外灰蒙蒙的。女儿在百无聊赖的做针线活。
餐桌:女儿端来土豆,女儿依旧慢条斯理的吃着土豆,但父亲用手只吃了半个土豆。便继续回到窗边继续看向窗外。镜头也推进到父亲的背影。
黑暗:黑暗突然降临,女儿点灯,父亲似一直坐在窗边。女儿在电灯后坐在床上。
油灯特写:油灯慢慢熄灭。
黑暗:女儿再一次点灯,可不管怎么用火去点油灯都无法获得光亮。光已然失去。
“为什么你不把油加满呢?
“是满的”
黑暗:黑暗中父女二人上床睡觉,黑夜里只有他们盖被子和呼吸的声音,除此之外只有沉默。风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第六日
餐桌:室内已失去光,沉沉的黑暗降临在头顶让人无法喘息,焦虑和绝望在几乎没有动作的长镜头中蔓延开来,外面风已经停了,只剩下黑暗中的沉默,父亲说着“吃吧”然后咬下生土豆。世界的崩坏已失去了火焰,女儿绝食反抗。影片结束。
全片共30个长镜头,多次的场景切换。才有了《都灵之马》的镜头语言。
关于“风”
狂风是影片中的摧毁者,问题的根源,它象征着阻碍人们生存的力量。而随着马的停止干活、绝食、井的干涸、灯的熄灭,在第五天晚上困境已经到达了顶点,再也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可言。此时击垮人的已经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精神状态。因此起着表征作用的狂风停了,留给人的空白直抵生存问题的根源:父女俩的生存窘境是天生就有了,人类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存在”本身。有了狂风的停止,才有第六天女儿的绝食。
关于父女为何又周而复始
可能是小镇已经被风吹跑了。父女二人已经无处可去了。也可能是马已经丧失劳作力,马车是由女儿艰难地拉着,狂风又如此肆虐,他们根本不可能走得了多久,离开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挣扎。
关于毁灭
传说神用6天创造世界,我想象一个相反的过程。” 贝拉·塔尔说,也就是说,《都灵之马》描绘的是一个世界 “毁灭” 的过程,价值的坍塌,生命意志遭到剥夺,一切都趋向贫瘠,狂妄的风席卷大地;人们试图逃离却失败了,不得不回到原地,等待死亡来临。
关于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可能是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里《极丑的人》,一群无神论,虚无主义者。这些人不是超人,但已经是新人,拒绝任何来自神或人的怜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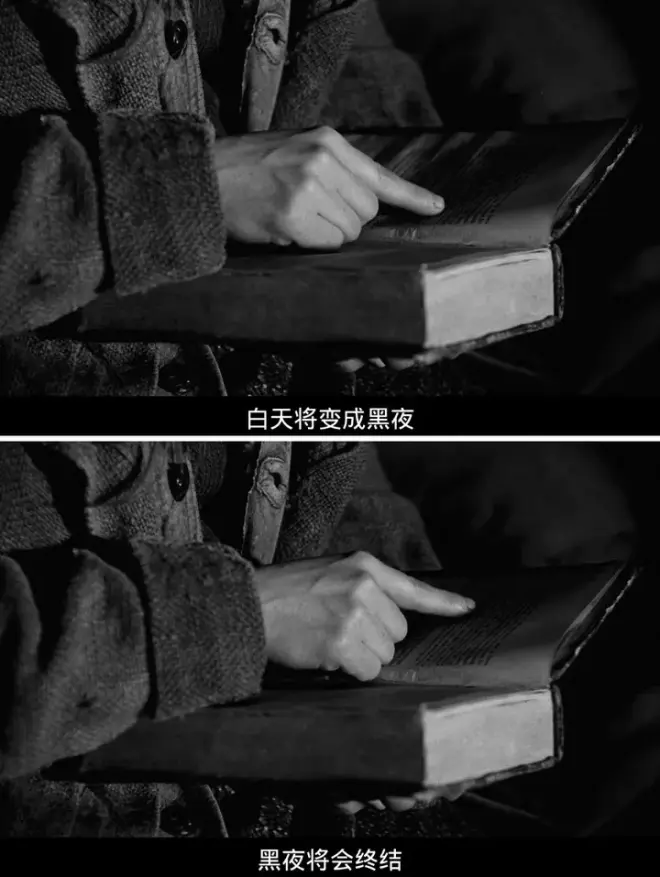




2023.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