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曹杨新村-第一个人民新村,追忆过去的时代
如今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某个小区的名字的时候,往往首先搜索到的是很多的租房买卖房信息,而不是这个小区所在地块的区划以及历史,这是我不大喜欢的一点,也是我写这一系列文章的原因之一。但是当我们搜索曹杨新村的时候,会发现在曹杨新村尤其是曹杨一村租售房的信息却寥寥无几,反而可以搜索到很多关于其历史的描写,我甚至可以说,曹杨新村的历史变迁从某方面讲就是中国工业的变迁,那就让我们将历史的时光拨回到70年前,去寻找关于这座工人理想村的历史痕迹吧。
1949年前在劳动人民聚居的普陀区,工人的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最低的还不到1平方米。1949年后上海得到了解放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 “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的指示,确定普陀区为重点试验区,贯彻“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市政建设方针”的经验,并组织工作组到普陀区帮助工作。为了解决职工居住问题,政府决定建设“二万户”职工住房,规划了曹杨等九个工人新村,开创了上海城市规划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而曹杨新村便是各个工人新村中最先规划实施建设的,如果说到这里大家还不能理解曹杨新村的伟大的话,一个更离谱的点就是曹杨新村作为一个“村”,竟然有一个村史馆,只是这个村史馆目前没有开放,如果它开放的话我也会拜访的,关于这个村史馆我们也只能通过图片来感受了。
曹杨新村是标准的从农田上建设出来的楼房,选择在城市郊区建设工人住宅,也体现出工人阶级并没有能够占据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核心空间。建国后,上海大体上维持了旧有的城市空间形态和社会空间结构。原位于城市中心的商业、文化区域被新的党政机关、部队军委、事业单位所占据。而与此同时,随着上海的工业外迁,对社区的工业人口进行疏散,第一批工人新村、企业住宅的建设,旧的城市空间与新的城市空间形成了“中心一边缘”的关系,并逐步固化。

1952年6月末,新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新村的首批住户正式入驻曹杨新村,他们无疑是光荣和自豪的,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一线工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002户人家,来自217个纺织厂和五金厂,分布在普陀、闸北、长宁三个区,每个工厂只能分到四五户入住。在住房条件普遍较差、“滚地龙”遍布的1950年代初,曹杨新村无疑极具吸引力。尽管三个家庭共享厨房和厕所,但对于当时那个没有自来水以及没有民用电、电时代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梦想中的生活。这里的房内铺着木地板,有煤气可用,出门绿树成荫,流水潺潺,不远处就是大学以及文化宫,是一个标准意义的工人社区,好不快活。
我们不妨打开1952年6月25日年的《解放日报》,下面的这几组照片便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历史照片,这组照片也作为了那些年新中国的一组重要外宣手段,虽然这些照片在现在看来摆拍痕迹有那么一点明显。其中第二张照片的一对工人夫妻拍摄了一组连续的图片,现在在曹杨新村的红桥处仍然存有与这座照片类似的雕像。


曹杨新村的建设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951年一1952年建成的曹杨一村,以及1952年一1954年建成的曹杨二村至六村使用了美国的邻里思想,而从1956年到1958年曹杨七、八村的规划便己经有了苏联大街坊式的影响,曹杨九村直到1977年才建成。
曹杨新村是一个样板,这种分配方式背后是示范的力量。首批住户就是最真实的榜样,向自己身边的工友们展现着生活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一起好好生产建设,大家将来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曹杨新村”作为新中国新建的第一个人民新村,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先后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多个国家的首脑、政要和旅游团队。这些颇有仪式感的环节,让居民们渐渐有了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对工人们来说,这自然是无上的荣耀。而这种居住环境,也加速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潜意识中的道德约束,也使得邻居们关系密切、互帮互助。一时间,曹杨新村堪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曹杨新村在那时的中国成为令人羡慕的“豪宅”代表,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70年来,曹杨新村已经成为一个承载着无数记忆和光荣的名字。这里是人民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地,“邻里单位”规划理论在这里首次落地,全市第一家工人新村商业网点、室内菜场、学校、卫生所,全国社区商业示范街兰溪路等等。这里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成果汇聚地,也是基层管理服务的创新探索地,曾被市政府命名为上海市“十面红旗”之一,成立了全市第一家社区党员服务中心、垃圾分类等改革破冰工作。
因为房屋年久失修,曹杨新村在2019年经历过了重新修建,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曹杨新村已经不是50年的样子了,但是改建过程中房屋仍然尽量的保存70年前的样子,改建于2021年底完成,采用原拆原建的方式进行。如今的或许从外观上看起来曹杨新村这些三层的小房子平平无奇,甚至可以说有点工业化装饰的普通。这里虽然已经不再繁华,但是在村口仍然红星高悬,门口有不少阿姨爷叔在三三两两的聊着天,我没有打扰他们,只是静静的感受,这里带给我的力量,这里小区旁边小鸟叽叽喳喳的叫着,几乎在说些什么,让我们穿越回70年前,穿越到现在。
关于曹杨新村这里所发生的的故事,互联网上任何一篇文章都讲的比我好,在这里我更多的是抛砖引玉一下,如果大家对于这部分知识感兴趣的话,大家不妨亲自去查找一下,我们还可以从新闻中对于曹杨新村居民的采访中看出更多的信息,这部分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好的,我在这里做一些总结比较个人化的总结吧,就说一下“社区的空间聚集感”。[1]
曹杨新村代表着什么?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
曹杨新村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在空间形态上留下了国家意志与规划智识相互博弈的痕迹,展现了国家治理空间化的具体实践过程,意识形态对于空间的渗透,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给上海的城市空间打下的深刻“烙印”。曹杨新村从规划、建设到使用的全过程无不体现了其具有的住宅社区建设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双重意义。新村在初期采用美国“邻里单位”规划理念,之后采用了苏联“大街坊”规划思想,在选址上既注重与工业区和市中心的关系也体现了工人阶级与核心权力在空间位置上“中心一边缘”的矛盾与博弈,新村内部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的标识性和方向感,住宅结构具有经济性、标准化、易复制等特点并极力压缩私人空间,强调了一种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
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验的重要典范,而工人新村作为新中国成立至今城市空间变迁的缩影,见证了国家制度改革、城市规划实践、产业结构调整等多方面综合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中个体与空间的相互建构的过程。在“工业型城市”建设的思想主导下,曹杨新村的住宅设计是以“先生产,后生活”的基本原则进行的。在“一切为了生产”的指导思想下,住宅只是作为生产之余的休息提供必备的场所。住宅是空间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曹杨新村的规划和设计,作为一种空间生产方式在单位制为主体的生产、生活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对空间的制度化改造为场所赋予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和意义,大大强化了其内部居民的集体认同。这种日常生活模式不同于农村,也不同于城市的开放,而是一种封闭性的、均质性的“工人文化”、“大院文化”。
说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结束本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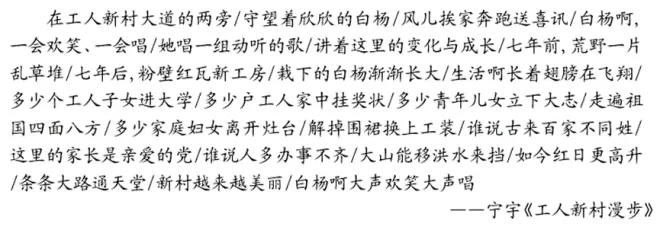
本文初稿完成与2023.3.23
参考文献
[1]齐文. 空间,场所与认同[D].中国美术学院,2017.
[2] 杨辰,辛蕾.曹杨新村社区更新的社会绩效评估——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J].城乡规划,2020(01):20-28.
[3]罗岗.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91-96.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07.06.013.
[4]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9%E6%9D%A8%E6%96%B0%E6%9D%91/5443431?fr=aladdin
[5]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d4y1X7uP/?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c337bb965cd645e6e2036a24d67cf07a
[6] http://www.shpt.gov.cn/caoyang/cy-sqdt/20220624/844149.html
[7] https://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baijiahao/2021/10/27/570971.html
[8] http://sh.people.com.cn/n2/2021/1101/c134768-34984590.html
[9]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c3MjYwMQ==&mid=2650698510&idx=1&sn=4dba9c4460f1fddc9aa47953329f56d5&chksm=bede3f5889a9b64e17bd1ac0a857d691adaee6bb6bf7cee31e27926f4d0d76202f733e224350&scene=27
[10]http://www.shwmsj.gov.cn/shssdq/2021/07/12/6e823709-e5e1-485d-9779-01d36e7a43b4.shtml
[11]http://epaper.routeryun.com/article/index/aid/3604620.html?searchword=%E6%9B%B9%E6%9D%A8%E6%96%B0%E6%9D%91
[12]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5136864

